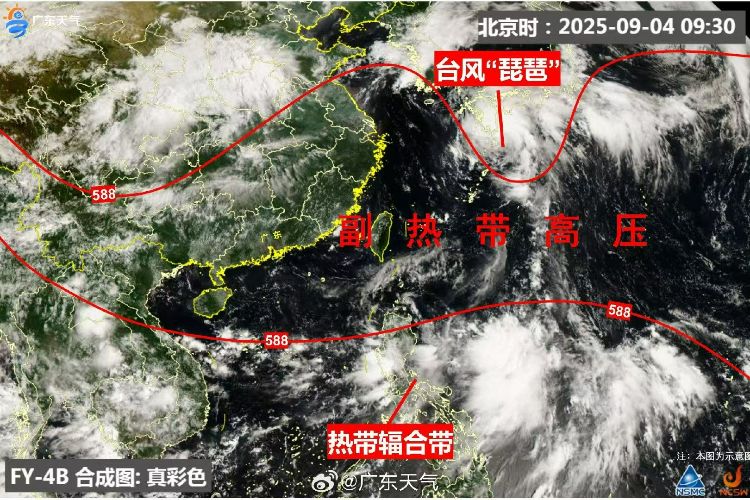乡村露天电影
小时候,村里每月照例放一场露天电影。那时电视机还没有,即便有也是稀罕物。每一场电影便成了全村人难得的大众娱乐。
放映的日子,多是白天晴好,晚上有月。下午或傍晚,斜阳西照,看到两挑放电影的铁皮箱子进村来。地里弯腰忙活的村民,放学路上贪玩的学生,豁了牙在门口晒太阳或闲坐拉家常的老大爷老太婆,年轻力壮的后生,春心萌动的姑娘,在溪边撸起袖子洗衣洗菜的俏媳妇,无不满眼喜色,“嘿,今晚放电影!”这条新闻瞬间成了村里头条。
黑框白底的银幕,在村小操场边树杈间一挂,就等于敲响了开场锣鼓。大家早早收拾停当,踩着月光,携带板凳,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往那儿汇集。
带板凳,太碍事,小孩子们嫌麻烦,耽误玩的工夫。我们一聚堆,叽叽喳喳,像一群张开翅膀乱飞乱撞的小鸟,游鱼似的在人群里钻来穿去,喜欢拥到亮着光源的放映机下面看稀奇,挡住镜头比手势,看银幕上投下各种怪趣的影子。有时,一条高脚板凳的影子四仰八叉出现在银幕上,引起一阵哄叫:“谁的凳子,快放下来。”小孩子嘛,小腰身小屁股,坐不坐不紧要,坐哪里也好解决。我们顺势坐上墙头、稻草垛、树杈等高处,或像蝙蝠似的一溜挂在教室的铁窗户上,有个挨屁股的地方就好,只求够高,不被遮挡视线。后半程,小孩犯困打瞌睡,偶有失足的,被大人们追着赶着打骂,在某处响起几声揭开锅似的号哭,准是谁犯事,当众丢了丑,被大人揪了耳朵,挨了荆条。黑灯瞎火中,父母找自家孩子的呼喊,或丢了板凳,破了脏了新衣裳,吵着要到代销点买糖吃,或家长想提前退场而小孩不愿跟着回家,诸如此类,打打骂骂,吵吵嚷嚷,一锅烂粥。
战斗片,大人小孩都喜欢。每次放映热场的科学种田、杀药除草的小短片,人群中总暴发急不可耐的喝倒彩:“师傅,卡掉,卡掉,直接放正片。”每当银幕上好人身处险境,人人屏声敛气,不知哪个小孩猛地一声喊:“注意,背后有坏人啊。”引发周围一片压抑而释放的笑声,大人呵斥:“别捣乱,放电影呢,演戏做戏——假的。”
有时,看着看着,原本坐在前面的后生和姑娘就不见了,板凳上空空如也,父母着急四处喊,四处找,可偏偏无人应答,不知躲去了哪个鬼地方。最坏的是村里几个“愣头青”,爱瞎起哄,悄悄去抬某个姑娘的凳子,或趁人家起身时不注意,一把抽开,好让人一屁股跌坐到地上,出洋相。有的姑娘偶有中招,回转腰身,一脸嗔怒,“愣头青”们嘿嘿怪笑,却无人承认,或是嬉笑中,追追打打就跑出了人堆。
有一次,电影散场,在操场后边厕所前的草坪上,两个后生大打出手。中间挡着我们的村花,正左拉右劝,她着急地嚷着:“你们两个不要打了,不要命了哇。”走过路过的大人们,竟没人上去认真劝架。小孩子偏着脑袋走过,满头雾水地问:“为啥他们要打架?”大人说:“鬼知道,爱打架呗,饭吃多了不消化。”小孩子想一想是有道理,牛吃饱了,就喜欢斗角。
那时只要听说有村子放电影,不管十里八里,年轻人成群结队打着火把,走夜路一两个小时都赶场似的去。我也想去,父亲黄着大眼一瞪,我就吓住了,乖乖缩回来了。也有被错过的电影,赶过去时,已灯亮散场,黑暗中远远望见树上挂着一面雪白银幕,看电影的人正四散往回走,我只能顺着回来,一路偷听别人边走边讲故事,但心里仍像看完了一整场电影似的心满意足。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徐向东 二审 韦多加 三审 黄廉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