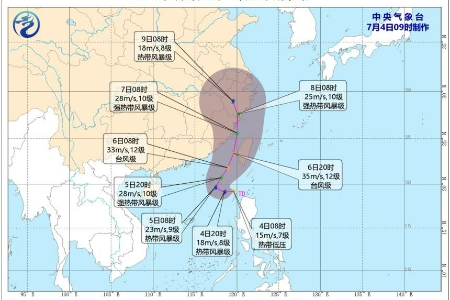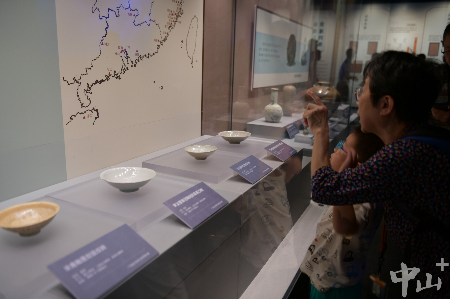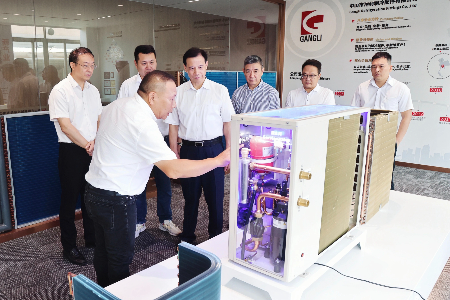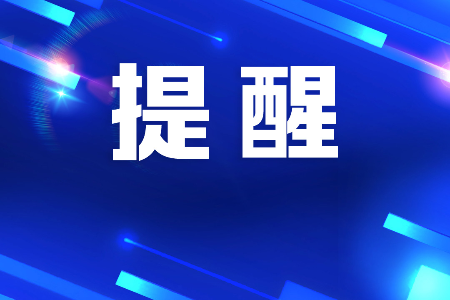去年九江的冬天,似乎来得早一些。十一月底,已是叶枯草黄、风寒水冷。当我冒着严寒匆匆赶到沙河殡仪服务中心时,岳父已入殓。灯火通明的大厅里,人声鼎沸,他安静地躺在棺木里。轻轻揭开盖在他脸上黑布,锥心的悔疚突袭而至,泪水瞬间奔流直下——如果我提前一天回来,就能见上他最后一面,几十年翁婿之缘的句号,或许能画得更圆一些。
岳父从起病到去世,都出乎我们意料。去年黄金周开始时还没有任何征兆,所以小舅子夫妻俩自驾到厦门游览,并从厦门一路游来中山看望我们。不巧的是,小舅子还没有离开中山,十月五日一大早,岳母打来电话,要妻子回去一趟,说岳父想她了,这是我们迁居中山三十多年来首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几十年来,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岳父几次大病住院,我们都是事后回去探亲才知晓。顿时感觉不好,急匆匆订好高铁车票,忐忑不安过了几个小时后,又退掉车票改乘飞机。当我们心急火燎赶到九江人民医院时,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病因是五年前发现的、而且以为已经治愈的食道癌复发。肿块堵住气管,导致进食困难、说话困难,甚至呼吸困难。医生征求我们的意见,要求切开气管。我满面悲戚地望着躺在床上的老岳父,他将食指勾起来,比了一个9字,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九十啦,你们不要难过”。我早知道他达观的生死态度,八十岁时,他就为自己的后事作了周全的安排:亲力亲为备好了全套寿衣;老家罗垅重修祠堂,他全力资助支持。交代我们说,他死后就停灵祠堂,葬在故乡。
切开气管几日后,情况似有好转。从咽喉科转到市人民医院新院区的肿瘤科,妻弟夫妻以及他的几个姐姐,衣不解带守候在身边。我们乐观地估计,至少还能在一起过个新年吧。在九江人民医院守了十来天后,见情况稳定,我便一人返回中山。但是死神没有留给我们这个机会,而是将永远的离别,安排在一个多月后的寒冷冬天,也将无以弥补的遗憾留给了我。
岳父的葬礼分两个阶段。为了方便他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区朋友、同事,他的遗体先安放在城区的沙河殡仪服务中心三天三夜。守灵的除了亲戚朋友外,更多的是岳父原单位的同事。他同辈的同事多已凋零,来到现场吊唁的同辈老同事、老朋友,都已年近九十,他们步履蹒跚,恭恭敬敬地上香、磕头,程式一点不差。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老岳父退休近三十年了,原单位还有那么多同事在寒夜里来通宵守灵。在寒冷的长夜里,大家围坐灵前,轻声细数他老人家几十年的人生,送他最后一程。
由于我离开岳父生活圈子太久,来吊唁或守灵的人们,多数我不记得,或本来就不认识。当知道我们翁婿关系后,话题就一下子打开了。他们讲起了岳父为人、为事、为官的许多故事,短短两三天,竟复盘了他几十年的人生经历。
岳父年幼时,读了六七年私塾,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新生政权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十五六岁的年纪,被招入了县土改工作队,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工作一年后,他又考进了九江师范学校,以后岁月里,入党、进修、转岗、晋职,再转岗,先后在财政局、供销社、监委、组织部、教育局、乡政府(公社)、一中、文化局等多个单位转圈,真是党锻造出来的一块好砖头,哪里需要往哪里搬。1966年32岁时,就担任了县教育局的副局长。
我与他的缘分挺奇怪的。1977年我读高中,学校在乡政府(当时称公社)边上,他是那里的领导。印象中他高高瘦瘦、身形挺拔、不苟言笑。他当时是不是分管教育,我不知道,即使他分管教育,也不会认识我这个毛头学生。一个周日下午我返校,刚出村口,见他推着一辆自行车,走在窄窄的湿滑的田埂上,鞋子上是泥,车轮上也是泥,样子颇为滑稽。我们的村子藏在城门湖边上的一个小山沟里,平时人迹罕至。见到他,我颇为惊讶,同他打声招呼。他笑着问,“你认识我呀?”我说,“认识,认识,你是当干部的”。他说,“不,不,我今天不是当干部的,我今天是钓鱼的。”他自行车上绑着钓具,看样子这一天收获颇丰,兴致高得很。十几年后我成了他家女婿,他的垂钓爱好仍在,多数周末的一大早就出门,到晚上才回来,脸被晒得黑里出油。
他的爱好其实是生活所迫。他和岳母的那点工资,要养育四女一儿,还有几个老人要赡养,生活挺艰难。前面几十年基本没涨工资,直至20世纪80年代,工资增长也极其缓慢,而且政策奇怪得很——上级给一个单位按总编制数下达增资指标,比如说本次增资指标是单位的30%的职工可以升一级,20%的可升两级,其余50%的暂不调整。为了那一级几块钱的增资额,不少单位打破人头,领导与职工严重对立。那时,岳父是县第一中学的书记兼校长,且按资历也完全符合增资条件。有一锤定音的权力,却多次将本属自己的指标让出来。他说:学校内大知识分子多,他们贡献大,优先给他们涨工资是合理的。后来学校盖了十几栋两层小洋楼,全部分给了那些高学历的老教师,岳父没有去要一套,而是一大家人挤在岳母单位的宿舍楼里。他在一中当主要领导十多年,那些上世纪60、70年代从上海、南昌等大城市,因落难而在一中任教的大知识分子,一直对他这个小知识分子恭敬有加,异口同声说他是个大好人。士为知己者用,整个80年代,是那所在江西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学的高光时刻,高考成绩一直不俗,清华、北大、复旦之类的名校,都有一中的学子。收入低、子女多、负担重,只有自己想办法。他上山打猎(那时还未禁猎),下河钓鱼,在城里边角处开荒种菜,有一段时间,甚至还在家里养鹌鹑,千方百计改善子女们的生活。前几年有个副镇长,用业余时间开网约车而受处分,社会上对此事分歧较大,以致酿成一个不大不小的舆情事件。初闻此事,几十年前与岳父在村口偶遇的场景立即鲜活起来。想起岳父那几十年的生活之路,感慨万千。我判断这个副镇长,不会是个坏官,至少不会是个坏人。
三十年前他临退休时,我曾笑问过老人家:你当官几十年,又当好人几十年,有什么秘诀?他教给我八个字:与人为善,克己慎行!那几天一波又一波来吊唁、守灵的人们,让我又想起他讲过的秘诀。这就是盖棺定论吧!
岳父的遗体在殡仪服务中心停放三日后送去火化。跪在告别室里,亲眼看到他的遗体被推进火化楼。妻子几姐妹大声地哭喊:“爸爸,你快点跑,快点跑啊!”估计是家乡的风俗,希望他早一点跑过奈何桥,早日重返人间。而我却在心里默念:卸下了世间所有的羁绊,您老人家慢慢走!
岳父的骨灰盒被安放在罗氏宗祠的大厅内两天一夜,这是葬礼的第二个阶段,天南地北的同族宗亲都赶回来了。岳父高龄辞世,对宗亲们而言,算是功德圆满,他们将岳父的后事当成喜事来办,俗称“白喜事”。祠堂内外摆满了花圈,请来的乐队吹吹打打,似乎并没有多少悲哀氛围。灵前升起几盆炭火,人们围火而坐,有的高声谈笑,有的窃窃私语,谈论的多是岳父这一生与家乡罗垅的交往。罗垅是个大村,从商从教从政的人数不少,其中出类拔萃的也有一些。岳父是最早走出这条山村的,他们这些后来者,或多或少都受到岳父的影响和帮助,有些人说到动情之处,潸然泪下。岳父凡事讲原则,外人看来似是个极古板的人,但他乡情之重,却又是众人皆知。岳母多次开玩笑说,这老头一生帮人无数,却从来不说出来,别人也不一定知晓。人是情感动物,哪有受恩而不知?只是有些人记在心里,有些人表露于外;有些人知恩感恩,有些人不屑于齿罢了。妻子上高中前后,罗垅有几个小孩也在城里上学,当时学校无法安排住宿,他们就和岳父一大家人,挤住在岳母单位那套宿舍里,直至完成高中学业。这次操办岳父葬礼的总管,就是当年住在岳父家、并与妻子同年被大学录取的兄弟。丧礼期间事多且杂,不巧他的妻子重病住院。他两头奔波,疲惫不堪却无怨言。人啊,血总是热的!
妻子的姐妹们多次聊起,岳父年轻时是个工作狂,对子女要求严格,对四姐一弟一视同仁,即使是对独子也没多出一分溺爱,他们从小就惧怕他。但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我女儿刚出生时,他已从学校转岗至文化(广播事业)局任局长,每天下班后,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急匆匆咣当咣当地跑过来,抱着还软绵绵的婴儿,满眼宠溺地看着,一边转圈子一边小声哼着不知什么名儿的曲子,一抱就是大半天不松手。妻子嘀咕道:这小家伙哪里修来的福气?我们小时候可没有这待遇。岳母也附和道,是呀是呀,老头变了啊!
1992年,为了讨生活,我携妻将雏离开了家乡,来到南海之滨的中山。我知道他是多么的不舍,特别不舍才两岁多一点的小外孙女。所以,1993年暑假我们回家探亲时,将小家伙放在他们身边半年。那半年,小家伙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那台傻瓜相机,存留了许多难忘的时刻。翻看以前留下的照片,成为我们后来几十年宝贵的谈资。知道妻子爱吃腊味,每年的春节前,他必亲去市场采购肠衣和瘦肉,自己动手制作腊肠,晾晒之后邮来中山。我们多次劝说:您年龄大了,不要再劳神,现在超市有的得买呀。他不听,三十一年,一年未空。对子女的爱,他拙于或羞于口头表达,于是就将爱铸进日常,越至暮年越重。
去年在医院切开气管后,因病痛折磨,又不能用言语表达,有时他十分烦躁。那时我女儿的儿子还不到2岁,正是牙牙学语之时。我将视频用手机放给他看,他立即安静下来,满脸都是笑容。我们似乎找到了灵丹妙药,于是将大姐的小孙子,二姐的小外孙女,还有我的小外孙的视频,一遍又一遍地放给他看,让他暂时忘去身上的病痛。在他去世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第四代三个小孩接连出生,还有一个已孕育于母体即将出世。我想,这是他接近人生终点的最大慰藉吧。
岳父大人,2023年11月28日早上走了,享年九十。五天之后的12月2日下午,在他的子女亲朋的哀哀声中,在整村的宗亲簇拥下,在连天的鞭炮声里,葬入故乡土地。草木荣枯,人世代谢,他已与大地融为一体,而我的思念却绵绵无期。只要想起他,我就想起他的教导:与人为善,克己慎行。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500字以内,欢迎短文,可配图,图片必须原创。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方嘉雯 二审 周振捷 三审 黄廉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