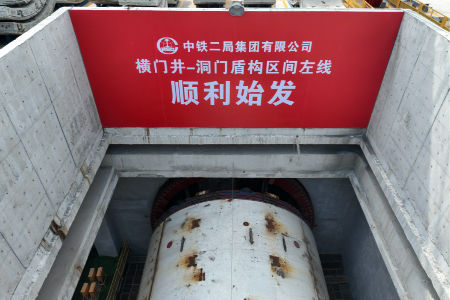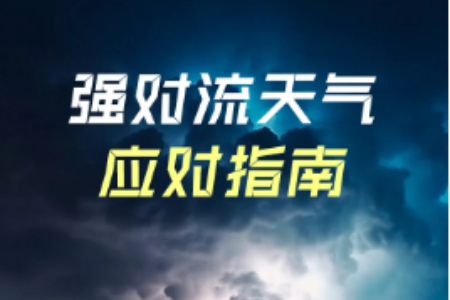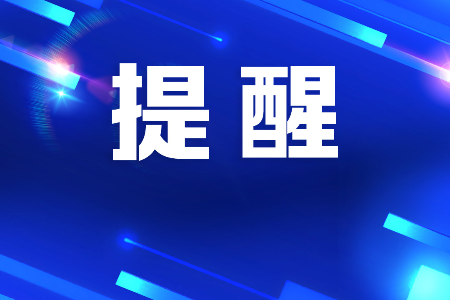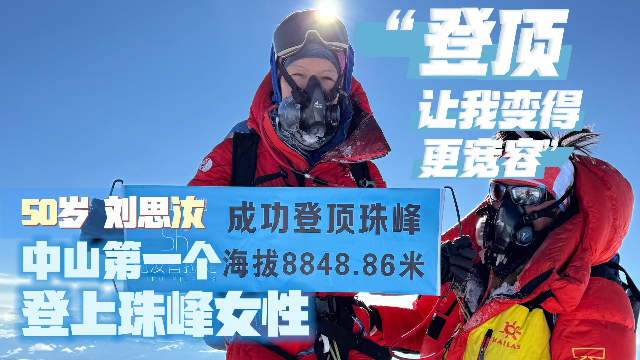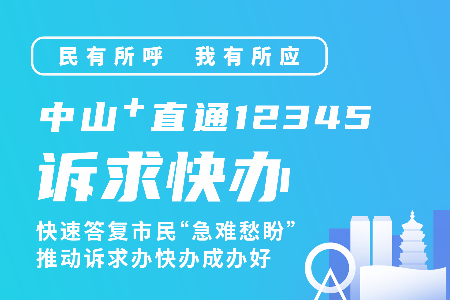三角梅之忆
一直对三角梅情有独钟。这种南方常见的花,春夏秋冬,都是花期,仿佛季节更替,与它毫不相干。若单独折下三两朵,那薄薄的几片红苞,并没有什么看头。当细小的花朵缀满枝头,远远望去,简直就是喧闹的飞瀑;慢慢走近,看得久了,繁密的花朵又似乎化作成千上万的蝴蝶,在风中翩翩起舞,一时间,会把人看呆了。
从前,陈森伟老师的家门口,就有一株三角梅,长势旺盛,占了大半个门面,那一片热烈的玫红,经常引人驻足。我对三角梅的喜爱,正是自这一株始。
追溯起来,我与森伟老师的渊源还挺深的。刚上小学时,上我们体育课的就是他。记忆中,每逢有他的课,我们都盼望下雨,下很大很大的雨,那种顷刻能将祠堂里的天井注满水的雨。如果天公作美,成全我们,我们就不用早早到祠堂外集队,而是端端正正地坐着,等候他笑眯眯地走进教室。这个时候,我们就一齐喊:“讲故事!讲故事!”我们的热情,总能打动他。他往讲台上一站,环视一周,干咳两声,教室里霎时安静下来,大家便心照不宣地挺直腰板,将双手叠放在课桌上,以最端正的坐势,静候一个故事的降临。他讲《鸡毛信》《西门豹治邺》,慢吞吞地讲着,却能把我们的心紧紧拴住,至高潮处,自己一点也不急,倒把我们憋坏了。
其实,我们也挺喜欢上他的体育课。他不单带我们玩各种游戏,还说如果大家的表现足够好,就教我们一套“少年拳”。后来,果真信守诺言,旷埕上,我们列队,扎马步,每出一拳,就喊一声“嘿哈”,路人纷纷注目,旁边那两棵老榕树似乎也被逗乐了,身上的黄叶纷纷抖落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得意了,吆喝声也更响了。
这些,都是40年前的旧事了。
1997年秋,我和森伟老师成了同事。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年头,而他已跨进教学生涯的末端,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看起来,他的形貌倒没什么大变化,依旧高高瘦瘦的,只是做起事来,与教我们“少年拳”时相比,迟缓一些,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我们都担任初一级的班主任,又一同上语文课,还住同一间宿舍。日常相处,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热心肠。开学之初,便将手头正用着的教学参考书塞给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还指导我刻写蜡纸。将空圆珠笔芯磨去珠子,代替铁笔。我一试,嗞嗞嗞,果然比铁笔顺手多了,又不易刺破蜡纸。不久写错了一个字,顿时傻眼了,抬起头来望向他。他心领神会,二话没说,点上一根烟,抽两口,徐徐吐出烟雾,再戴上老花镜,不慌不忙地用烟头来回烫几下,变戏法般,蜡纸又完好如初了。我在内心暗暗赞叹,老前辈们的办法就是多。很快,平生第一份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油印试卷出炉了,他轻脚轻手地抽出一张,在同事间传递着,一个劲夸我悟性好,上手快,字写得漂亮,夸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备课时碰到的困惑,也总能及时从他那里得到满意的解答。他告诉我,侧面描写嘛,就好比要写教室里的静,却转而写有人从外面走过,以为里头一个人也没有。如此深入浅出,我现炒现卖,课堂上一抛,因为很应景,学生们瞬间就领悟了。至于班级的管理,姜还是老的辣,他传授给我的,就更多了。那时的我,太年轻了,凡事急躁冲动,幸得有他不时的提示与规劝。刚踏上讲台,能逢上这样的引路人,感觉很幸运。
一来二去,一老一少,渐成忘年之交。
每个早上,我和森伟老师总是最先到达办公室。我提了两个大水桶,到校门右侧的手摇井盛水;他则着手收拾办公桌。满满两桶水提上三楼,茶具也清洗干净了。一天的工作,就在氤氲茶香中开始。这样的生活节奏,一年里几乎日日如是。
午饭后回办公室,依然一泡茶,两人边喝边聊。他性情内敛,平时话不多,甚至有些少言寡语,初看近乎口讷。一旦被他引以为知己,却有说不完的话,有时聊到兴头上,常有妙语冲口而出。相处久了,发现本质上,他是一个浑身都是幽默细胞的人。我们在一起,我喜欢充当听众,他有一肚子的段子。举凡本土掌故、传闻,都熟记在心。而最为精彩者,则是其家族史。我经常听得入了迷,以至于有时产生一种错觉,仿佛穿越到幼年时,雨天里他给我们讲故事的场景。茶喝足了,瞌睡虫开始袭来,回到房间,躺下,他继续刚才的话题,直到发觉我进入梦乡,才停了下来。
这一幕幕,真是让人怀念。
时间之水的冲刷下,森伟老师讲过的那些故事,好些似乎已经模糊了。直到两年前,我应邀到他的村子,采写一个全景式的乡村故事。端坐在村委办公室的四五位受访者,年长的已近九十,最年轻的也有七十多了。他们的任务,是给我讲述乡村的过往。或许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这些见多识广的长者,还是有些许紧张,这让他们的话语更加失去条理性。就这样轮番讲着,又七嘴八舌地补充着。慢慢地,我终于理出了头绪,却越发觉得惊心,整个乡村的半部文化发展史,无论他们怎么反反复复绕来绕去,居然大都绕不出森伟老师这一家族。
他的祖父,就是清末秀才陈若虚先生。1911年夏,一场罕见大水,将北溪河秋溪堤溪头至溪边段冲毁了,这就是潮汕地区历史上著名的“辛亥水”。时任秋北堤公所董事长的若虚先生,耳闻目睹,深为痛心,遂上呈陈述灾情,博得上司怜恤,拨下巨款,修复决口,恢复生产,乡民无不交口称赞。也正是这一年冬,若虚先生在村前的河边高地上,创办了时术小学。为勉励学子,还亲撰一副藏头联:时光可贵莫虚度;术学有成唯实求。厚积终于等来了薄发。1946年,潮安县小学较艺,时术小学一举夺魁,“时术”之名,一时大噪。这是我们家乡教育史上的高光时刻,捷报传来,举乡欢腾。乡里请来两个潮剧戏班,还开设灯谜一台,象棋赛一台,是夜,整个村子陷入欢乐的海洋之中。
父亲陈贤源,曾在当时集广东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陈济裳手下担任要职。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一回,一身笔挺戎装,骑着高头大马,在荷枪实弹的侍卫的簇拥下,回到家中。“秀才公”一见,大为不悦,不给儿子好脸色看。此后每次返乡,常衣着朴素,形同普通人,至村口,随即下马,独自步行,一路上和乡亲们打打招呼,聊聊家常。这就是家乡民间广为传颂的“秀才教子”故事。
若虚先生的外甥刘文鸿,幼时曾入时术小学读书,亲聆舅父教诲。1989年,在暹罗经商有成的他,独捐人民币60万,重建时术小学。据他动情地说,此前舅父曾托梦于他,再三叮嘱,务必倾尽全力,续写时术小学的辉煌。言辞恳切,醒来思之,尤其动容。
这些故事,其实我早已烂熟于心。采访结束后,我还沉浸在刚才的振奋之中。与老人家一一握手道别之后,遂独自一人,到与村委会仅一墙之隔的时术小学走走看看。早已过了放学时间,校园一片寂静,唯有各种花卉竞相开放。快步踏进陈若虚纪念堂,抬头就看到正中位置上,悬挂着陈若虚先生的遗像,面容清癯,双眼炯炯,神色庄重。隔着岁月的烟尘,我与先生长久对视着。步出纪念堂时,才发现右墙角一株三角梅开得正好,一大簇繁花,骑在高高的墙头上,仿佛一束熊熊的焰火。一下子就忆起唐代著名诗人张若虚《迎春》一诗中的诗句:“含蕊红三叶,临风艳一城”。诗中多少带着些夸张成分,而眼前所见,确实足以惊艳半个乡村。我心有所动,又回过头来,望了一眼纪念堂,感觉对若虚先生的理解又深了。
那一次采访,彻底激活了我的记忆。这才发现,好多记忆其实并没有被我遗落在人生的来路上,而是一直完好地封存于心灵的一隅。一个偶然的机会,再次打开来,才惊喜地发觉,它们依然鲜活着。
退休之初,我到他家多次,他也回访了一回。我们都很珍惜这一缘分。每次晤面,依然无话不谈,情分并没有随着分开而降温。记得有一年春节期间,他家刚好来了一大拨客人,他还把我让到楼上,两个人单独聊了起来。稍后,他随儿子长居外地,见面的机会越发少了。虽然不常联系,彼此心里却一直惦念着。
犹记得当年在办公室里,聊至特别投机时,森伟老师多次悄悄对我说,余生最大的愿望,是将家庭史弄成一部长篇小说。我一听就来劲了,也特别期待,还经常帮他出谋献策,我们暗地里连标题都拟好了,叫“弯弯的北溪河”。他出身书香门第,有一定文学功底,又教了半辈子语文,我相信他是有这个能力创作出来的。而且,又是退休在即。退休,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正好调整状态,集中心思,写它个昏天暗地。
可惜退休后,他得过一场大病,动完手术,虽保住命,人却更消瘦了。2014年9月,终于一病不起,走完生命的历程,享寿76岁。这些,我都是事后才获悉的,因此,竟没有在他住院医治期间,前往探望,略表寸心。每每思及此,常常引以为憾。
疾病所揽走的,往往不只是健康,还有一个人的斗志。大约因为身体原因,影响了他的心境,心心念念的长篇小说,迟迟没有动笔。回过头来看,这应该是他人生的最大憾事吧。直到写作那篇乡村故事,我趁机将其家族史捋一捋,作为重头戏,编了进去,算是稍稍圆了他的心愿吧。内心深处,又有一点小小的期待,希望这个家族的故事,让更多的父老乡亲看到了这背后延续的传统之力,看到其中的“礼”,找到某种力量。
行文至此,不禁又忆起森伟老师家的那株三角梅,只是后来房子改建,那一大架三角梅也一同被毁去。如今,每次从他家门口经过,我总会忆起舒婷的那首《日光岩下的三角梅》:“只要想起/日光岩下的三角梅/眼光便柔和如梦/心,不知是悲是喜。”我的头脑中,就会浮现起那一片红云。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徐向东 二审 向才志 三审 岳才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