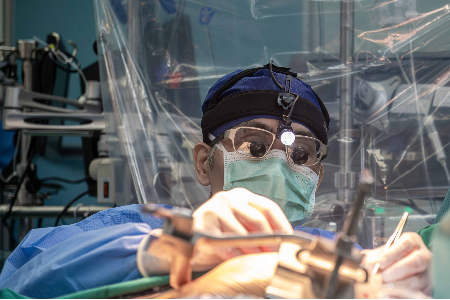临江仙
家住西域冰山,告别了世界至高屋脊下的豪华玉宇,以浩荡的奔流之身荡开了一条蜿蜒之路。一路上,惊的雷、暴的雨、电光石火,都无法喝令他改变自由奔放的习性和寻找出路的斗志。当他疲惫地和我们擦肩而过时,早已不是富家弟子,而是一个衣衫褴褛、面色醋黄的流浪儿模样了。
牵牛车、服力役般的劳累和艰辛,使他历练成为旷世的诗歌达人。但真正读他、懂他的人其实真不多。无奈,他在距东海龙宫百里之遥的海之门畔、在一个叫临江的古埠对岸,一面抖落了叫作凡尘的一盘沙土,一面以悦耳涛声开路,高举风的经幡,轻装入海。
这是若干年前的故事了。确切地说,故事开头,这里的人类活动才刚刚开始。但每当听到家门口的江水复述一次,我就增加一次对这些名沙名洲的美好向往。好在这里水陆交通发达,欲看一块被诗歌巨人驻足和怀抱过的永隆宝地,驱车前往也仅为一两支烟的功夫。
未曾隔江犹唱半句“后庭花”,却隔岸吟咏过一首探索永恒的哲学诗词,词的牌名应该就叫“临江仙”。
当年途经临江的大仙吕洞宾和他的座驾鹤舟,早已随一江春水踏歌而去,但古词的血肉还在:“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个静坐江边,看彼岸花开的小镇仍在,正有了临江小镇的日夜相守,前往梦幻之岛才如此便捷。
踏进一方圣土,饱览一隅风情。永隆,沧海到桑田的示范田、样板片,亦如握于大江之手的掌中宝,不大犹小,八平方公里而已。
岛龄尚年轻,所以这里尚没有诸葛庐、子云亭等名胜古迹。对天张望的港梢,也了无张献忠沉银宝船类传闻,如有,也仅是几艘明清时期沉没在口口相传中的官窑碗舟,可谁能打捞呢。但也有无需打捞的,原住民沿用了几百年的沙里方言和老了牙的敦厚乡情就在那里,被龚自珍称为先啬的陈朝玉当年率众越江而过,以绳断担落为记,垒灶埋锅、垦荒种地,直至炊烟起如海云的创业故事也在那里。
江天水色。白墙黛瓦的民居在雨后阳光下越来越美,漫过青春期的树木一天比一天茁壮。树有灵、万物皆有灵、一灵则百灵。朋友从远方来,不亦乐乎。喜欢自然禽鸟的,他们渴望的品种将会越聚越多,小河里黑天鹅有了,白天鹅还会远吗?说不定,不远的将来就有东南飞的孔雀,西南来的凤凰,北归的鸿鹄,东来的丹鹤,西去的青鸟等珍禽异鸟在此落脚生息;喜欢诗歌诗词的,这里就会有杜甫的茅庐、李白的月亮、李清照的藕花鸥鹭;喜欢摄影的,鱼戏莲叶、鲤鱼吃荷花或飞鸟叼鱼的视觉盛宴或将准备中;想独看这边人文风光的,除却浩渺无垠的江景,还有一个个令人陶醉的浪漫小站,一切比你想象中的好;即使被沦为吃货,那些源于活水,让人叫不上名的鲜货,足以让你一饱口福。总之,你来与不来,他们都会在一个叫“情深深、雨蒙蒙”的路口,端举着醇厚的风情之酒,等你迎你,不醉不归。
欲把江岛比海岛,我还是选择江岛。谁受得了夕阳下从外洋上空恍惚飘来的咸涩风信?而被江水流年淘洗的永隆小岛,最起码的空气也牵扯着唐古拉山的云蒸霞蔚,清冽中带着冰川的丝滑和雪莲的幽香。我更喜欢岛上旷野中迎风而舞的岩兰、香茅和野花,只一闻,仿佛让你回到了热恋的佳期,想起那雅得沁人心肺的美人体香。
当然了,也喜欢风情的奥伦达部落,绿野仙踪。那些如草原毡房一样四平八稳的房车,幽静宽敞,整装待发的车轮神态欣然。此刻,只需一匹双峰骆驼即可重返昔日丝路。而骆驼呢,一定被一串铃声唤去了远方。而它的客人,正在弯月下搂着一片蛙声入诗入梦。
在一座欧式的玫瑰园,觉得自己就是个白马王子了。才举起手中的相机,许多的红花绿叶,偶尔也有几朵白得让人忌妒的花蕾,纷纷昂起高贵的头和我形成对视关系,并以轻风中摩擦的低语,或对我评头品足,或争吟一首关于花开花落的小诗。也许,她们在乘我按下快门之机,早已把邂逅的信息发送到了朋友圈,或收藏在一朵名花的心底。
如是,待到他乡再遇故知时,其花一定更娇美,其叶一定更悦人。
(不收微信来稿!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山日报社媒介拓展中心
◆编辑:徐向东
◆二审:向才志
◆三审:岳才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