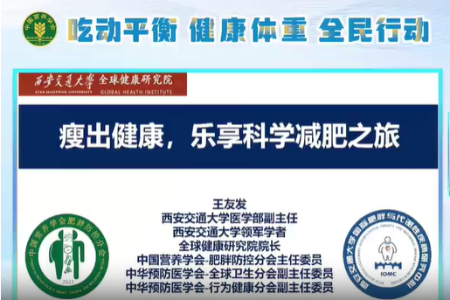《香山叙事:上海四大百货与中国近代化》创作笔谈
当《香山叙事:上海四大百货与中国近代化》的创作,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疫情环境中的创作实属不易,它不仅束缚了我的手脚,也限制了我的思绪。
但是,收获也蛮大,除了巨量历史资料的攫取和消化,特别对创作中的“在场”有了新的理解与发现,并做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感觉就像“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心房蓦地空灵了敞亮了。
纪实文学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所谓纪实,主要强调事实的新闻性,即作家所呈现的一定是新发现的有价值的多维在场。有人认为,在场是作家与新事物的密切接触或身临其境。
从理论上讲,这话没错。
问题是,在场是一个很复杂的哲学命题,密切接触或身临其境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现在很多纪实文学作家就陷在这种困惑中,请问100年前的事情,作家如何在场,难道你真的能穿越时空吗?有些作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好找隔壁家的二大爷采访,因为隔壁家的二大爷的三姨夫的父亲,曾经与书中的主人公有过工作联系,看起来似乎找到了在场的抓手,实际上这种在场很蹩脚,而且容易丢失信息,导致以讹传讹。
历史题材的密切接触或身临其境很难,也做不到。隔壁家的二大爷再多,也解决不了密切接触或身临其境问题,因为历史场景已经被时空掩埋了。与其如此,倒不如将“隔靴搔痒”转化为发掘历史真实和研究历史资料上。
我曾经写过一部新闻理论专著《新闻超限战》,在这部书中,我深入解析了史态新闻所蕴含的巨大现实意义。它表现为历史对现实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既包括价值取向,也包括文化记忆,前者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基本要素,后者构成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素质。因此,无论是历史书写抑或书写历史,作为一种权力,在具体操作上都相当于对历史符码的重新建构。
海德格尔认为,时间在本质上并不是“现在系列的前后相继”,而是“在当前、曾在、将来中嬉戏着的在场”。据此,我们将时间的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将来,对应移植到事件在历时上的三种状态:史态、现态和趋态,并以德国学者伽达默尔的“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来加以关照,就形成了我们的史态创作观。
史态创作观是对历史题材的超常规认知与表现。
历史自有其独特的魅力,它千姿百态,令人陶醉,历史题材向来都是以人的活动和活动成果为观照对象的,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一般而言,历史自身的魅力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继而激发人们进行深入研究与书写。之所以说理解的历史性构成理解的偏见,缘由在于认知主体所处的时空已经远离了认知客体,原原本本复原认知客体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认知主体只能依据自己所处的时空来理解认知客体。因此,伽达默尔补充说“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
历史题材的创作,说到底是作家对历史中蕴含的新价值的认知与表现。它是历史记忆与精神守望的共契,是历史与现实的价值连接,它就像炮队镜与坐标点一样,每时每刻都标示着社会前行的各种数据,为前行的人们矫正航向。所谓的“以史为镜”大概如此吧!
因而,历史题材的创作重在价值发现,当然此过程也融合着多层思维的在场。有人对多层思维做过精彩剖析:即从二界思维到三界思维,从单向思维到多向思维。漫长的人类历史证明,人能够认识事物,源于人接受了由事物发出的信息,而信息则是表现事物特征的普遍形式。可贵的是,信息具有可复制性特点,它一经产生便可相对独立于母体,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可能:人们对某一段历史的认识,不一定以接触某一段历史来完成,而是通过接受复制过的信息来达到同等目的。
事实告诉我们,除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信息世界,人们通过复制的信息来认识事物,而代替直接接触历史本身,这就是“二界思维”向“三界思维”的演进过程。在人们所掌握的知识中,由紧密接触或身临其境获得的知识毕竟有限,大量的知识是通过相对独立的信息获得的,比如书籍、史料、师承、祖传等。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历史题材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历史题材的鲜活度和饱满度。因此,历史题材的在场要比现实题材的在场复杂得多、立体得多、精彩得多。
历史题材的在场,重要的是新认知、新价值的在场。文学创作本质上是新认知和新价值的书写,而非纯客观事物的整体描摹。我们经常迷失在客观事物中,认为客观事物才是文学的主体,实际上并非如此,客观事物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存在,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往往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家只能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进行书写,作家的在场只是认知的在场和价值的在场。
《香山叙事:上海四大百货与中国近代化》前期准备的时间很长,2010年2月,中山日报与上海《新民晚报》联合策划的大型系列报道《中山人在上海》启动,我站在上海南京路,看着曾经繁华的先施百货大楼和永安百货大楼,心中无限感慨。从那时起,我萌生了书写上海“四大百货”的想法,但随着有关信息的日积月累,我觉得上海“四大百货”已经被人写尽了,超越前人成为一件很难的事情。直到2022年春节前夕,我正准备去海南岛过节,大脑突然闪出“上海四大百货与中国近代化”的字样,我很兴奋,即刻拨通了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宋钻友先生的电话,他认为这个题材很好,至今无人涉猎过。节后,我从海南岛回到中山,宋钻友先生寄来的书籍和资料也收到了,他的支持和鼓励坚定了我探索上海“四大百货”新认知和新价值的信心。
如今,百货大楼在中国星罗棋布,但它们的根脉还是上海“四大百货”,而且,就其对城市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以及人的心理空间的影响而言,后继者似乎无法超越上海“四大百货”,这也是其至今能够傲视群雄的重要因素。
新认知和新价值的在场,是历史题材最重要的特征。至于是否采访过隔壁家的二大爷,其实并不重要。试问,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采访过隔壁家的二大爷吗?但他们写出了传诵千年的历史巨著。道理很简单,他们在历史信息的街巷里游历得久了,发现了前人没有发现的被历史尘埃掩埋的新认知和新价值。
历史题材的创作,至今不出其右。
而贯穿新认知和新价值的是思想在场。思想是一种优越的思考方式,它往往通过逻辑推导来搭建价值体系。有人把这种方式叫作思辨,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黎光先生的作品当属此列。如《大国商帮》《中山路》《横琴》等,都是思辨特色鲜明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自己的思想将“历史珍珠”串联起来,进而形成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历史是一个无限时空,它既连接着历史,也连接着现在与未来,历史是昨天的现在,现在是未来的历史,因此历史具有多元性,浮在表面的是浮游生物,游在中间的是虾兵蟹将,沉在底层的是巨型生物。其实,每个层次都有每个层次的美感和价值。秋风塞北,春雨江南,人情冷暖,世故变迁,皆是美的所在,作家的责任就是将你所发现的美,通过思想建立起美轮美奂的精神殿堂。
文学说到底是一种思想苦旅。没有思想在场,就不会发现新认知和新价值,有什么程度的思想,就有什么程度的认知和价值,这就是文学的精彩所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上述诸多在场,又是粘合在情感场域之上的,只有情感充沛的场域,才可能更好地展现新认知和新价值。这就是情感在场,仿如雄鹰翱翔于蓝天,飞得越高看得越远,看得越远越能发现更多新认知和新价值。假如飞得越高空气越稀薄,你还能发现更多新认知和新价值吗?文学情感恰如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文学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如过江之鲫,其作品更是汗牛充栋,而真正流传千古的大都是激情四射的作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文学情感从来都不是“依啊哇呀”的咏叹,而是驱动作家思想与行为的动力之源,在社会生活中,每个身心健康的人对情感都有强烈的需求,这种欲望尽管复杂,但更多的时候表现为激情。泰戈尔说:“激情,是鼓满船帆的风,风有时会把船帆吹断,但没有风,帆船就不能航行。”
作家是需要激情的,尤其要避免“民工式”写作,因为文学是情感的产物,有感而发才可能惊天地泣鬼神。美国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也觉得激情是一种意识状态,能够鼓舞和激励一个人对手中的工作采取行动。他评估一个人的时候,除了考虑才干和能力,非常看重一个人的激情。因为有了激情,创作才可能有血有肉,作品才可能光芒四射。《香山叙事:上海四大百货与中国近代化》是否具有这些元素,本人难以判断,还请各位读者品鉴。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500字以内,欢迎短文,可配图,图片必须原创。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方嘉雯 二审 周振捷 三审 黄廉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