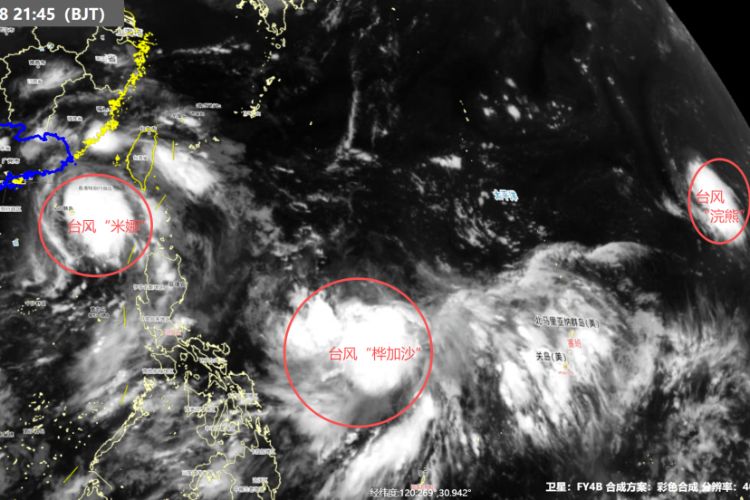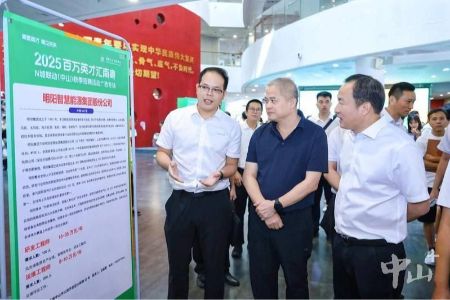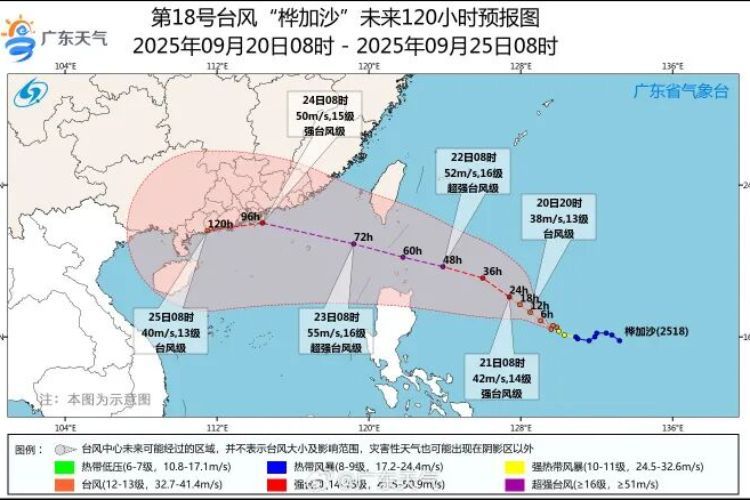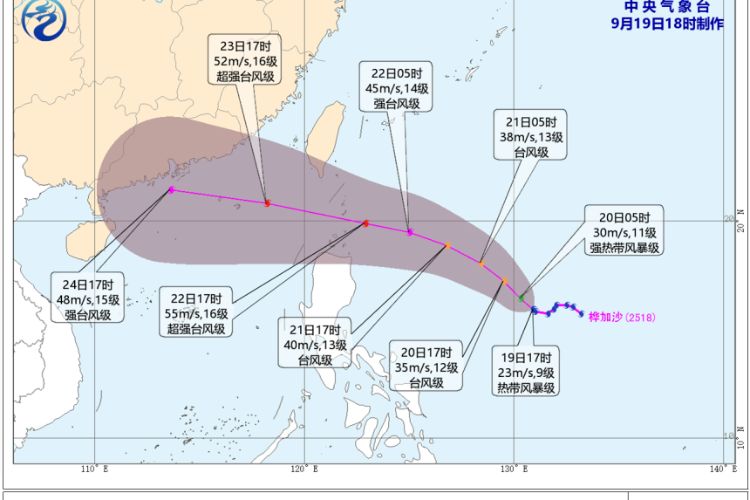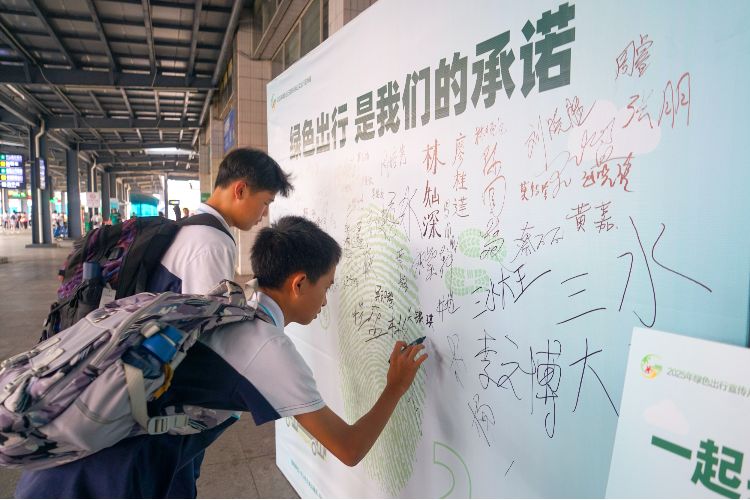这几年在“佩兰文艺”的公众号里读中山女诗人张佩兰的诗,总让我想起“残雪”两个字,深究其中原因可能是她的诗写得好,不事张扬,却自带清冷的光芒。她的诗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却像秦岭深处的残碑,借用她的一首诗为例,每一道刻痕里都藏着亘古的风霜与倔强的生机。若用一个词形容这种独特气质,“诗意的残雪”或许最为贴切:既有冰雪的清冽孤绝,又有消融时浸润大地的细腻温柔。
她的诗中,古典韵律的基因与现代白话的肌理奇妙地交融,在“散文化”成为新诗潮流的当下,开辟出一条兼具传统风骨与当代精神的路径。《过秦岭》一诗最能体现这种特质。开篇写“‘山’字太轻浮,‘岭’字太纤弱”,以五字句短促顿挫,像极了古诗“炼字”后的决断,每个字都带着推敲的重量落地。诗人用“玄铁般的残碑”替代轻飘飘的文字,让“沉默”成为比语言更有力的表达。石面“风蚀的篆文”与案头“怯生生的幼苗”般的诗句凝望,这种对比戳中了创作最本真的困境:面对秦岭“莽莽苍苍的脊梁”,文字不过是“风化后抖落的尘沙”。
但诗人的妙处在于,她让这种“无力感”生出力量。长句与短句的交错,如同山风掠过沟壑的节奏:“一个嶙峋山骨召唤整座秦岭;一个欲向沟壑夜枭的低鸣”,对称的句式藏着古典对仗的影子,却不用严格平仄,只靠语义的张力与呼吸的停顿,让千年秦岭的厚重在字间流动。结尾“青铜沉处,千山显形”“钺锋上残留的一声虎啸”,用留白的力量打破文字的局限,恰似残雪覆盖的山骨,沉默之下仍是奔腾的血脉。这种用白话的“形”承载古汉语“气韵留白”之“神”的写法,让诗既有现代的直白,又有古典的余韵。
若说韵律是她诗歌的“骨”,那对创作与生存的深刻叩问便是“魂”。《关于写诗》以诗观诗,将创作喻为“骨缝里暗燃的火种”,精准道破诗人的精神处境:“语言的贫瘠,你如此对抗着空白里凿出的沟壑”。这里没有浪漫的想象,只有“灼伤指尖”“蛛丝悬峭壁”的痛感——写诗成了一场与“失语”的苦役,是“秋蝉在将熄的盛夏尾声嘶鸣”。但诗人偏要在“子夜时从血中捞出沉坠多年的旧砝码”,将其锻成“刃口朝向自己的静默”的薄刃。这种“以刀刃向内”的执拗,让“写诗”超越了技巧,成为精神存在的证明,像残雪在寒冬中对抗消融,冷硬中藏着滚烫的内核。
她的诗不缺人间烟火气,却总能在日常中提炼出“柔软的停顿”,让残雪般的清冷多了份温热的质感。《活在向阳的山坡上》里,“一杯酒浇进喉间,烧出一条向阳的小径”,醉意化作“锄头”,从“骨缝里掘出多年前埋下的晴日”。那些“被季风说烂的祷词”,终在“麦浪的起伏”中重新造句。生活的粗粝在自然韵律中变得柔软,恰似残雪消融后,土地里冒出的第一缕生机。
《鞋子丢了》更是将这种“停顿”写得妙趣横生。“赤脚踩气流”的他被世俗视为“贪玩孩子”,却被“我”一眼认出,“嘘,别声张”的默契让两个异类在沉默中相认。诗人“偷偷试着成为它”,“让风穿过空荡的肋骨”,将肉身的沉重化为羽翼的轻盈。结尾“梦里领养了象群与兔群”,让不被理解的孤独在万物共生中找到归宿。这种对自由的温柔向往,像残雪覆盖的旷野里突然飘起的纸鸢,清冷中藏着叛逆的诗意。
在“散文化”常被等同于“随意”的当下,诗人佩兰的作品恰似一面镜子。她证明真正的诗性自由,在于用内在节律框住生活的呼吸,用精神张力赋予文字重量。读她的诗,如同在残雪覆盖的旷野中行走:脚下是冻土的坚硬,耳畔是风的回响,抬头却见纸鸢在云端轻舞,骨缝里的火种与向阳的麦田共生于同一时空。这便是“诗意的残雪”——不迎合潮流,只忠于内心的节律与万物的回响,在冷硬与温柔、古典与现代的交织中,为当代诗歌留下最动人的留白。
(本文作者铁舞系上海作家,诗歌评论家)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500字以内,欢迎短文,可配图,图片必须原创。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方嘉雯 二审 周振捷 三审 黄廉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