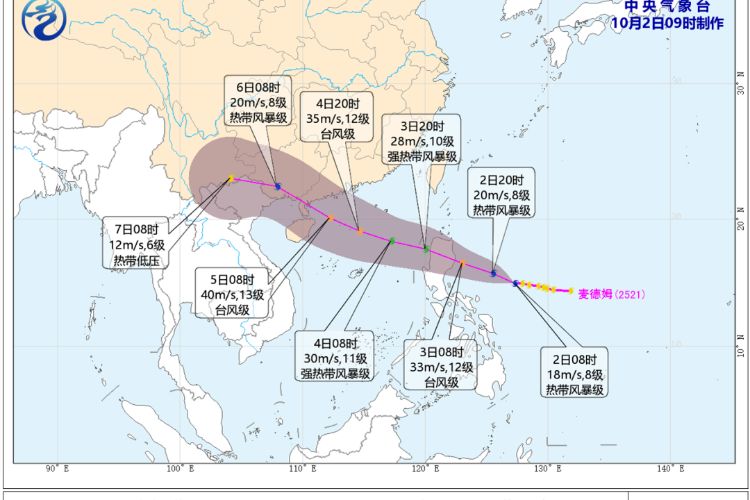关于怕
又到开学季。没想到我的成长与“怕”有关。
同事中有极怕蛇者。倘是路上瞥见便拔腿就跑,倒也不足为怪,见到影视作品里蛇的场景便紧捂双眼,也是情有可原。偏偏是家里的书,凡有蛇的图片,家人都要一律替其剪去。更匪夷所思的,是每每于书中看到“蛇”字,便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几欲把书本抛至户外。
小时候,蛇我倒是半点不惧,农村的男孩子,鲜有害怕蛇的。夏天的夜晚,我们还常常带着手电筒、铁钳、蛇皮袋等工具,结伴绕着村里的几个鱼塘夹水蛇,配合默契。胆子大一些的伙伴,还会拎起水蛇的尾巴抖着玩,将蛇玩弄于股掌之中。我最怕的要数“北狗”(南方一种类似于狼的凶猛野生动物)。当年很多长辈都经历过路遇北狗的惊险一幕,这往往成了他们后来引以为荣的谈资,仿佛不曾遭遇过几回北狗,就显得见识短浅阅历不丰。晚上小孩子调皮,不肯老老实实入睡,大人们常常脸一沉,搬出北狗来吓唬我们,说再不听话,就任由北狗把你叼走。诸如此类的话,重复得多了,自是闻北狗而色变。
虽然像小说《祝福》中狼叼走“我们的阿毛”的一幕,始终没有在周边上演过,基于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平日里,祖母还是悉心地传授过我诸多防北狗绝技:路遇北狗,千万别慌,要沉住气,以进为退。北狗怕火,也怕嘈杂人声,点一根火把,就足够把北狗赶跑;人多时,大伙儿一齐亮开嗓子吆喝,肯定会把北狗吓得够呛的;又或者狠劲敲着脸盆锄头之类的金属物,也可以唬住这些畜生;至于爬上高树之类的,更是应急的好法子……但我觉得所有这些还远远不够,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我有了更具“威力”的应对之策:只消把我那写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草绿色书包在头顶上抡圆了,抡成一个白亮白亮的盘子,呼呼作响,我就不信北狗还敢上前半步。很长时间里,我很为自己这一发明激动不已,可惜稍懂人事时,北狗已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圈子,我始终没有遭遇北狗,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展示这项旷世绝技了,这不得不说是我童年的一个巨大遗憾。
后来是蚂蟥取代了北狗。那是上小学后,小伙伴们开始热衷于捕鱼。那时农村的水质尚好,水里鱼虾多且肥美。纵横水沟里,选上一截,两边用淤泥堵严,再用脸盆水桶戽斗之类的工具把里面的水舀干,往往就有小半桶的收获。但是,这个过程也伴随着风险,水蛇没有毒性,不足为虑,怕就怕偶尔被蚂蟥叮上了。它不像螃蟹钳人一样有痛感,而是无声无息地附着在你的脚盘或者小腿上,等到你发现有点痒,用手一摸时,它已经吸足了血,滚圆滚圆的,让人感到特别恶心,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用力硬扯下来,强大的吸盘还会扯下一小块皮肉,伤口便流血不止,更加剧了我们对蚂蟥的痛恨。而且,据大人们称,若发现得不够及时,蚂蟥还会直接钻进皮肤,进入体内,四处游走,甚至到脑袋里逛荡,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听得我们毛骨悚然坐立不安。
不过,捕鱼收获的喜悦,依然轻易战胜了对蚂蟥的畏惧,很多个周末,我们常常把时间挥霍在广漠田野的水沟里。真正使我对蚂蟥恐怖得内心发毛的,还是上初中那阵子。那几年,父亲在北溪河的滩涂上开垦了一块水田。滩涂本是溢洪之地,一场滔滔大水,便颗粒无收,乡亲们大都不屑于去耕作。父亲觉得在这里种植不用交田租,收多少是多少,因而铆足了劲,一有空就忙于扩充“领土”。像父亲这样的农民,只有家里的粮食垒得高高的,直至快要把屋梁顶起来了,他们才会觉得心安,睡觉才会安稳。
那时,家家户户最缺的就是劳力,十几岁的孩子,都要帮忙干些农活,给大人打打下手,下田插秧割稻一类更是常态。收割稻谷累是累,倒是还能忍受,最让我发怵的,还是插秧时节。那时还没有抛秧这项技术,只能赤足弯腰,在水田里倒退着插秧苗。这片溪沙坝上蚂蟥奇多,仿佛是这个星球上蚂蟥的大本营,通常刚跨进去迈上几步,提脚一看,就有好几条蚂蟥叮牢在脚盘上,即便是频繁移步如踩梅花桩,也丝毫无济于事。大概是沙地过于贫瘠,这些蚂蟥都饿得昏了头罢,插秧时,有时还有个别竟奋不顾身地附着到我的指缝里,软乎乎又冷冰冰的,让我一瞬间魂飞魄散,不断下意识地拼命甩手,似乎连那只手也不想要了。由于这一幕过于刻骨铭心,多年之后,我仍心有余悸,玩“植物大战僵尸”游戏时,常常会联想到“有一大波蚂蟥来袭”的场景。
父亲却仿佛视蚂蟥为无物,只一味专心致志地插着秧苗,很快眼前就是一片绿了。他插秧的速度快极了,简直可以称得上“无影手”,是我见过的插得最快的大人。即便是沙地,节奏也丝毫不减缓,以至于我常常突发奇想,如果参加农运会的插秧比赛项目,父亲肯定能够脱颖而出一露峥嵘。只在偶尔起身歇息的间隙,他才朝手掌吐上一口唾沫,把脚盘上密密麻麻的蚂蟥捋至掌心,顺势甩到远处沙地上。他这种对吸血蚂蟥的漠然无视,彻底消除了我打退堂鼓的念头。
这一次的“悲惨”遭遇,也揭开了我与蚂蟥斗智斗勇的漫长过程。听大人们说,蚂蟥最怕洗衣粉的气味,下一个插秧时节,我特意备了些洗衣粉,下田之前,先行在手脚上涂抹上浓浓的洗衣粉水。这法子果然绝妙,好一阵子,蚂蟥依然不敢贸然来犯,我不禁有些自得,暗自感慨办法总比困难多。正当我为自己的有备无患自鸣得意时,大概浸泡时间久了,手脚上这道临时筑起的防线开始失效罢,蚂蟥陆陆续续向我发起了进攻,我无奈只得重新回到田埂上,再次涂抹上洗衣粉。这一季的插秧,我不知上上下下了多少趟。父亲看在眼里,后来,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撂下了话:怕,怕就要专心读书。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下一季度插秧,我索性穿了一双已磨损了脚后跟的旧袜子,再用橡皮筋将裤管束起来,心里还颇为得意地想,有了这层实打实的防护措施,看蚂蟥怎奈得了我。可是,插完了秧苗,累得腰酸背痛的我坐在田埂上脱下袜子时,这才发现,脚盘上有滑溜溜的感觉,不知何时,袜子里已钻进了好些蚂蟥,六条,七条,或许更多。它们在痛饮了我的新鲜血液之后,一条条膨胀了好几倍,差不多要赶上我的手指一样粗细了,而且,墨绿间隐隐透着血红,显得更加光亮可鉴,仿佛一块软塌塌的玉石。我汗毛直竖,感觉双腿瘫软,仿佛被蚂蟥吸干了,一时间,真是无法计算自己的心理阴影面积。
1992年中考之后,我顺利考上中师。我自幼身子骨弱,经常生病,学习成绩又基本过得去,父亲一直希望我走读书这条路,今后有一份固定工作,软风软日的,不用像他一样,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没日没夜地操劳着。结果终于如其所愿,他内心的欣慰,作为儿子,我当然是多少能够理解的。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这些旧事没有顺应时光的流逝而褪色,偶尔忆起,我也会这样寻思,人活在世上,有一两样怕的东西,也不见得就是糟糕的事。或许,正因为怕,才能够让人更好地认识到生命的种种局促,进而产生敬畏之心,时时砥砺自己,奋勇前行。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题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徐向东 二审 韦多加 三审 岳才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