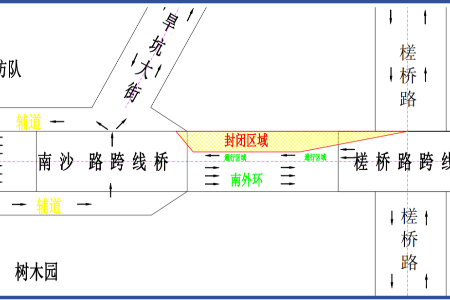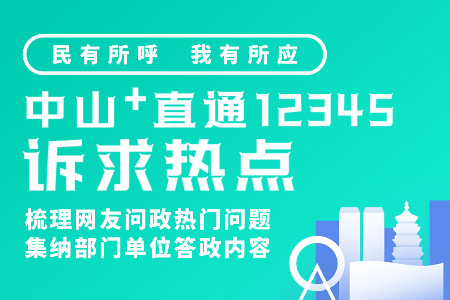一丛月季出墙来
斜阳有些吝啬,时阴时晴。大姑姐前面带路,我跟着她,在她童年生活过的铁路老家属区悠闲散步。错落的步梯楼房下,是七弯八拐的通达小径。
大姑姐忽然停步于一道静悄悄的院墙下不走了。我用手掌拂遮住眉梢上灼眼的光,定睛看她。她不像是在躲荫,也不像是在刻意等我,她是在看那一丛越过墙篱的粉花。
早先青灰砖上苔绿斑斑的墙壁,翻新后刷上了新白墙漆。白色是包容且奉献的中性色调,它活跃在各种背景配色中,呈现或衬托出对方的明亮度。所以,那丛淡淡的粉花,此刻远远地望去,也有格外醒目的色泽。
那丛粉得如夕日霞辉的花,繁复叠瓣,层层缩小,裹着黄细短线儿的花蕊,与一些饱含希望的鬲色花骨苞儿簇拥,参差着独立冲出墙篱向天而开;又归并着,摆出一副同根而生、相依相伴的模样。花模样像极了蔷薇和玫瑰,只有月季花心里知道,它就是开得最长久的月季花。
大姑姐熟谙花主人季红,她俩是发小玩伴兼同学关系。季红长相平平成绩垫底,除了大姑姐,几乎没有多余的朋友。母亲早逝,父亲所有的宠爱全给了季红弟弟。季红高考落榜后,按常理正好接替刚退休的父亲铁路工人的职位。然而,父亲却执意让季红弟弟辍学接班,把这个“铁饭碗”送到弟弟手上。
季红生父亲的闷气,不声不响由着一列夜行的火车,把自己当货物一样拉到了远方。
从此,她以跑南奔北的火车为家。
一小段一小段的时光叠加,像一节一节行驶中的火车车厢,承载着季红从少女到妇女的十几年生涯。
她在水泄不通、异味多多的硬座车厢里,兜售香烟、瓜子、啤酒、矿泉水的时候,撞到了一个卖画报的男同行。男同行眼神狡黠而犀利,教唆季红怎样逃过乘警查票、如何贩卖迎合旅客口味的假劣商品、哪种歪门进货渠道利润更高。季红被男同行一脸精明老练吸引,全然不问下一站,是驿路还是归宿。
直到季红与男同行的女儿要入户上学,才发现男同行另外有家,是一个负债的赌徒。先上车后补票,没了座位,季红带着年幼的女儿主动下车。她存册上数字后的多个零,也被男同行输得剩一个零。
季红父亲在遗嘱中留下的老房子,接纳了她们母女。
这一丛出墙的月季花,是季红和女儿一起种下的,当时只有一截根蔸露在墙角的花盆里。当时高铁已普遍开通,坐长途火车的人少了。季红不可能重操旧业谋生,她就在自家院子里,架起大铁锅,炸起了油粑子卖。湘南人不叫“油粑子”,叫套花与瓜片,本地的特色小吃,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晓得做,平日也当点心吃。用面粉、糯米粉搅拌,加白糖,搓成细条,绕成镂空花朵状,或是实心圆薄片状,撒上芝麻花生入热茶油锅炸,味道香脆可口,多吃容易上火。
季红油炸套花和瓜片的滚滚浓烟,穿墙四起,熏得邻里眼睛疼。大姑姐领着年少时那帮同学熟人,纷纷给季红捐款,季红分文不收。也许是生性自立好强,也许是努力在女儿面前活出尊严。令人欣慰的是:她现在过好了。有了自己的油炸小作坊,有了广源的顾客,女儿也考上了市里一所重点高中。
院门久久未开,我和大姑姐站在墙外,认真看了一回月季花:茎上暗红的小刺,锋芒毕露,惹得直想踮脚抻摘的路人放了手。花儿在翡翠般绿叶的映衬下,分外妖娆。此情此景,令我不自禁地想起了,汪曾祺先生一段关于花的小语:“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来稿请注明文体、作者真实姓名,以及银行账户全称、户名、账号和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等。文责自负,所有文章观点均不代表本报。)
◆中山日报社媒介拓展中心
◆编辑:徐向东
◆二审:韦多加
◆三审:黄廉捷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