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九曲河
“一天门、二门坎、三级石、四方井、五街祖庙、六家祠、七仙街、八卦巷、九曲河、十皇殿。”我喜欢小朋友用本土的石岐话一边轻快地跑着,一边高声地诵读这段顺口溜。难以割舍的乡土乡音啊!仿佛带人穿越时光隧道,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一切瞬间沉淀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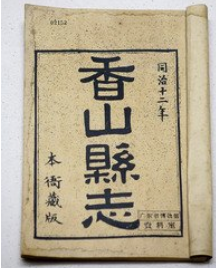
这是从前流行于香山(今中山)近两百年的地名顺口溜,指的是散落在中山城区及其附近的街道村落著名景点。这些旧时风物,有的至今仍在,徜徉其间,常会勾起思古之幽情;可惜,绝大多数都被现代化的浪潮吞噬或湮没,使中山这座城市的鲜明个性和特色明显减少。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九曲河,可谓中山人的心灵家园。曾经的小桥流水,人家枕河,船来船往,绿树绕墙,一直是优美的所在。曾几何时?九曲河被钢筋水泥覆盖,成为脚底下流淌的暗渠。如今只能只能纸上追忆,梦里寻回。
据《香山县志》记载:“云坛桥涌,源出良字都蟾蜍岭西,合双合山北峡水,至三角塘村前潴为罗婆陂。西折至库涌村前,桂峰、小岭水来会,至砚涌分流。一支迤北九曲入清风桥,绕文庙而西。又名九曲水。过元兴街为东濠,会东关水;又西过南门桥为南濠,会南关水,出登瀛桥。一支迤南折西,过桥仔头,又北为西边涌,东北至登瀛桥河流,过梅基,总名南河。出元坛桥涌前入石岐水,皆平流,可行小船。”
这里描写的“南河”,包括九曲水、东关水、南关水、石岐水。可见,南河并不等同于九曲河,而是包括九曲河在内的四条水道;九曲河也不等同于九曲水这一条水道。但由古至今,人们都习惯以“九曲”之名一统河山,将这些水道统称之为“九曲河”,南河反而淡忘了。“九”在古代不是实指而是虚指,很多的意思。九曲,其实就是曲曲折折,有很多弯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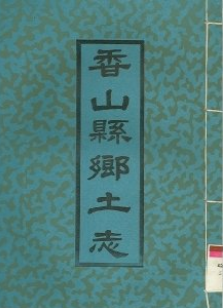
迄今为止,几乎写到九曲河的前世都以清道光年间的县志为依,并由此断言九曲河最早为“九曲水”,其实不然。九曲河最早的名称叫 “九曲溪”,这与它的源头有关,“源出良字都蟾蜍岭西”。蟾蜍岭是五桂山的溪涧,溪水充沛,由高到下,由东流向西,其终点是岐海,岐海亦今岐江。
有人说,中山人固执叫河为海,这就错了。以前的岐江的而且确是海,十分辽阔,是因长期淤积,慢慢变成今日的岐江河。从正在施工中的“石岐总部经济区”挖出的大量海蚝就是明证,唐代左丞相郑愚的诗《泛石岐海》上阙亦可佐证:
“此日携琴剑,飘然事远游。
台山初罢雾,岐海正分流。
渔浦扬来笛,鸿逵翼去舟”
这里的“台山”,指石岐以南的南台山,“岐海”指石岐海。寥寥数语,道出当时岐江原来叫石岐海,也曾是个大渔港,船来船往,颇为繁忙。
岐江河与浩瀚的伶仃洋相连,每当潮起潮落,九曲河都会呈现出倒流奇观。岐江涨潮时,河水倒入九曲河,水几乎与街面平,水流浩荡,由西向东,显现出壮观的景象,是为地地道道的九曲河;岐江退潮时,九曲河的水主要是五桂山源源不断的溪涧水,特别纯净,清澈见底,与河底奇形怪状的石头想映衬,美得醉人,太震撼了!晚上的时候,清溪映月,那种景象更是美不胜收。还是用明代著名书画家、香山诗人伍瑞隆的诗形容最为贴切:
“城边溪水碧如葱,城外扁舟渡晚风。
日落月来天在水,行人浑入镜光中。”
把九曲河称为九曲溪,最早的文献出现在明末的《九曲溪歌.并记》,照录如下:
“九曲溪者,县南之一水也。自西迄南曲折而走,不知其凡几百里。曰九曲者,数极于九也。溪之西則為長洲象角西丫諸村落,溪之南则为天王桥,富春里。其中烟树郁郁,人家如鳞,崩崖断石,朝夕有声;其上则荒城废垒,颓驿危庵。怀古之士,好游之客,过其水滨莫不唏嘘太息,忾慕当时。盖宋之季太后少时,帝亡入粤,自崖山至吾香山皆为驻师之地。此邑之人有马公南宝者,迎帝幸其家食荔枝。道由此水至今犹有太后遗迹祠于溪上,忠气义之气,盖虽亘千百世犹将与此水而无尽也。九曲云乎哉!虽然自宋而元自元而今日,其间帝王兴废,河山代谢,人事升沉,指不胜屈,独此水则太后少帝之旧游,马公南宝之故宅至今有能道之者将纵而观于汴京之宫阙,江左之偏安,始则壞国事于会宗,继则任平章于似道,英雄什佰无所措手足,生其时不亦难乎?古人有言,一日九断肠,闻斯语岂不谓然?而今而后游于此水,触于此情又将与此水为无尽也。九曲云乎哉。偶与友人停舟其下,循古道,读遗碑凭吊久之,为次其事并歌之曰:
九曲兮,水何之,肠断兮,一如斯。石矻矻兮树离离,西风悲兮吹我衣,我将起古人于九京兮,非其时。”
撰写此文的叫何巩道(1642年-1676年) 字皇图,号越巢,是明末和南明宰相何吾驺的儿子,曾任锦衣卫指挥使,颇有气节,抗清不仕;他对历史颇有研究,擅诗能文,是著名的爱国诗人,著有《越巢诗集》二卷等。
据何巩道的《九曲溪歌.并记》可知,从前的九曲河即九曲溪远远不只两公里,而是“不知其凡几百里”,很长。也很美,“烟树郁郁,人家如鳞,崩崖断石,朝夕有声”。并且,“独此水则太后少帝之旧游”原来,南宋皇帝与太后曾游九曲溪,当年何巩道言之凿凿:“至今犹有太后遗迹祠于溪上”。
何巩道此文不长,但文采飞扬,笔墨生香,触景生情处,异常沉重,心景悲凉。尤其是,字里行间慷慨悲歌,不得不令人思接千载,忆起了这个令人荡气回肠的宋王朝,这既是一个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与唐诗并峙的另一个文学高峰——宋词的朝代,也是一个创造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三大发明的年代,更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科技史上最出色最优秀的年代。
宋朝分北宋、南宋,南宋更是座拥全世界最先进科技文化和经济最发达的一个朝代。可是,在冷兵器的时代,“文明往往干不过野蛮,正统干不过流氓。”
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后,转而集中力量对付南宋。富裕安逸的南宋怎敌得过在血雨腥风中奔走的蒙古铁骑?宋帝在忠臣将士的护卫下,不得不亡命天涯,退至广东香山(今中山)。
公元1277年(宋景炎二年)的冬季,在寒风凛冽中,当地乡绅马南宝把南宋流亡皇帝赵昰迎进了沙涌家中,马家祠堂成为皇帝的临时行宫。此时,香山成为了南宋流亡朝廷最后一个喘息之地。
当此际,从朝廷到民间,不少人闻元色变,暗潜而逃。马南宝却反向而行,组织起勤王义军,成为那个时代的逆行者,开启他悲壮的人生!
当地乡民在马南宝号召下,竭力保卫皇帝,守卫严密,较长的一段时间,“元人不得而知”。所以,皇帝与太后得以游玩了当地名胜。可以想像,荡舟九曲河,优哉游哉、何等的轻松惬意!可是终让元兵侦知了宋皇行迹。很快硝烟又起,前线失守,皇帝在宋军的护卫下,撤到距沙涌村一百多公里的崖山。

公元1279年的那个春天,一点也没有变暖的迹象,萧瑟天冷,草木摇落,是谓“春宜温而寒,是春行冬令矣,实属不祥。”
在这个严寒的春日,宋元大决战暴发,宋军战败,宋少帝与十万之众将士跳海殉国,演绎惊心动魄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千古绝唱。
据传,少帝投海殉国后,第二天遗骸浮出海面,随着海水漂流至九曲河。让附近的华光庙一个庙祝发现,设法将其拖上岸,见是一童尸,身穿黄袍龙衣,认出是少帝赵昺的遗骸,庙祝忙与乡亲用本地的五桂山特产——沉香木做了一副上等棺材礼葬于五桂山。也许上天有灵,让少帝有所依归,漂浮至此吧。
宋亡,马南宝日隐匿不降,后寻机重举义旗反元,战败被俘后壮烈殉节,年仅36岁,明清两朝均追表其忠,崇祀乡贤。马南宝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其浩然正气万古流芳。
前尘滚滚、硝烟弥漫,连接着过去、承载着历史的九曲河,怎不令怀古之士,好游之客,过其水滨唏嘘叹息?
然而,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早已荡涤了九曲河的声声叹息。元灭宋后,侥幸生还的宋室遗民的优秀基因,散播于香山县的寻常百姓家;以马南宝那些英雄为代表的家国情怀,也影响着香山人的精神世界。从明朝始迄至民国,当地名人终于井喷般涌现,震古铄金者,如大学者黄佐、黄培芳,明朝宰相何阁老,中国第一个启蒙思想家郑观应,扭转乾坤的历史伟人孙中山,中国现代音乐之父萧友梅,博士之父王云五,百货业之父马应彪,空军之父杨仙逸,粤乐宗师吕文成等,入典籍的数以千计。
一河流淌,夹岸花香。九曲河荡漾起的情感浪潮,是老中山人解不开的情结,穿不透的红尘啊!
据老一辈回忆,昔日的九曲河就像“周庄”,颇具“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直至改革开放前,九曲河两岸还完整地保存着晚清和民国时期水乡风貌和格局。两岸民居依河而筑,依水成街。沿河两岸有古旧砖屋、木屋,横街是有宽有窄的街巷,左穿右行在石板铺就的小路,会有向过往岁月延伸的感觉。深街窄巷也藏着小食店小商店,街边小作坊里的杏仁饼香在空气中弥漫着,食店里飘出的红烧乳鹆香味,能让路人驻足、垂涎;偶尔听到的叫卖声,更显街巷静谧;拐角处,不知是谁在拉二胡,声音哀怨;走几步,又传出钢琴的声音,乐声悠扬,弹奏这个小城的惬意。
年少时,每逢周末常到九曲河附近亲戚家小住,居住在九曲河畔的石岐人,其房子都有石板级延伸至河水边,方便洗衣洗菜。正当夏季,很多人在这里游泳,小孩子在河边玩水嬉戏。我喜欢用纸折叠成纸船放下河里,任凭它飘向远方……
岸边堤围榕柳成荫,三五成群的人们在树下的凉亭石凳聊天。傍晚,凉风习习,三三两两的人们摇着葵扇,慢慢聚到河边,或站,或坐,或躺。庭院稍大的,则围坐着慢慢品茶,谈笑风生。对于久在职场,心生厌倦的人,看着小河流水,清风拂面,顿时神情气爽,豁然开朗,心境特别开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正是这样的写照。
河道上横跨有许多小桥,桥街相连。据长辈回忆,在当年的九曲河上,计有清风桥、南门桥、登瀛桥、悦来桥、元坛桥。这五座桥,暗喻“九五之尊”。上述小桥,最负盛名的莫过于位处柏山村的“清风桥”。清风桥由石板彻成,横跨于两岸之间,周围环境是一处风景胜地,茅舍修竹,荷田阡陌,蒹葭苍苍。最宽阔处水面达数亩,俨然一湖泊,水清如明镜,可见鱼儿游戈。
据传,清末民初,不管春夏秋冬,横风细雨,九曲河都有游艇穿梭。这些游艇,均称“紫洞艇”,实质是酒船,扮演着“风月”角色。在里面的人,对酒当歌,吟诗作画、猜拳行令和拨弄丝竹及对弈品茶,而清风桥一带河面是紫洞艇汇聚之处,文人雅士,坐贾行商每有流连于此,直至午夜亦有乐不思蜀者,盛极一时。
清风桥我未见过,想必我懂事时,清风桥已湮灭了。但 “登赢桥”给我印象最深刻,是单桥石拱桥,两侧石雕护栏,桥的半圆拱与倒影在水平的半圆形成一个整圆,远看仿似月亮,非常好看。太阳照在河面上,小船轻摇,绿影婆娑。那古老的登赢桥,守候着前世的相约,变成一幅绝美的风景画。
浅浅的风景,淡淡如诗。夕阳西下,青年男女喜欢在登赢桥这里约会。甚至,乌篷船也喜欢停泊在这一带,除了售卖鱼虾蟹,就是当地的农产品,如芋头、番薯,香蕉、甘蔗等。后来附近直接形成一个“登赢桥市场”。这些并没有破坏登赢桥的浪漫景致,相反觉得颇有人间烟火气。小时候,很喜欢到这一带玩,看临河老屋木窗里漏出来的灯光,听乌篷船里飘出的咸水歌。对这里的景象,我记忆犹新,曾有诗记之:
九曲弯弯午涨潮,渔舟夜泊登瀛桥。
凭窗晚唱疍家女,倩影波中分外娇。
疍家,又称艇户,是一种以船为家的渔民,世代以打渔为生。广泛分布于中山水乡地带。小时候读过的一首《蜑户诗》,就是描写疍家人的:
“天公分付水生涯,从小教他踏浪花;
煮蟹为粮那识米,缉蕉为布不需纱。”

那时候,九曲河里的鱼虾特别多,称为“疍家人”的水上人家棹着小艇网鱼虾,泊在岸边卖水果。船上的艇仔粥、煎堆、茶果等地方特色食品令人垂涎三尺。
说起艇仔粥,老石岐人最是熟悉不过。疍家人为了生计,以新鲜的河虾或鱼片为配料熬成粥,摇着小艇向游客兜售,艇仔粥由此而得名。
入夜,月亮时隐时现在薄薄的云层里,不时撒下淡淡的月色。阵阵秋风,掠过河面,带着水浪拍打着船舷,有节奏地响着。
河面上传来“艇——仔——粥”的悠长叫卖声。卖粥的疍家人一边摆划,一边高声地唱着:
“月色朦胧睇(看)唔(不)清,有心帮衬(购买)请开声”。
当灯火一家家地亮起来,将河边的房屋倒影在河面上,与慢慢行进中的摇橹小木船构成一幅小城多浪漫的风情画。耳边似乎响起了疍家女唱的咸水歌:
“日间有个太阳照,晚间有个月来朝。
荣华富贵我唔要,清茶淡饭好逍遥。”
“浮家泛宅”的疍家人安贫乐道的生活情景一下子浮现出来。说起咸水歌,其实是疍家人口耳传唱的口头文化。清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诗语》称“疍人亦喜唱歌”,而似中山等水乡地带,此种情况尤为盛行。
九曲河是不少疍家人赖以谋生之地,人们日常生活所思所想大多可以歌中发抒。记忆最深的是当时流传于九曲河一带的婆媳对唱,颇有意思。当时九曲河有户姓李的人家,娶个媳妇,希望生个男孩,香灯后继有人。谁知愿望落空。李家把责任都推到儿媳妇身上。一天早上,做婆婆的见儿媳妇正端一盆水洗脸,灵机一动,怨恨地唱道:
“朝朝洗面照颜容,颜容落在水盆中。
咁好鲜花无籽结,枉费孩儿开夜工。”
漂亮的媳妇是个聪明人,一听歌声聒耳,知道婆婆嫌自己入门后没有生育,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换个法子含蓄骂人。于是,她针锋相对的唱道:
“咁好禾田咁好坑,谁知你儿不会耕。
犁头不入三分土,倒插禾苗怎样生。”
婆婆听了,心想岂不错怪儿媳?故不做声。暗暗地唤儿问个究竟,方才知道事出有因。只好叫儿子求医问药,后来儿媳很快就珠胎暗结,不久就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龙舟鼓响,五月粽香。
端午节赛龙舟,这是石岐的传统习俗,地点就在九曲河。直至五十年代,一年一度的龙舟大赛都是在九曲河举行,并不是现在的岐江河。可见以前的九曲河一点也不窄。说到龙舟,这里姑且荡开一笔:
长期以来,大多数人以为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纯粹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在古代岭南地方,吃粽子、赛龙舟与屈原没有半毛钱关系。据《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可见龙舟竞渡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己存在。翻遍正史,也没有只言片语说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有关端午纪念屈原之说仅存在于野史中。而正史有明明确确的记载,端午节是为纪念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石岐人陈临。据《后汉书》记载,陈临任苍梧太守,政绩卓著,他去世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
岭南地区,尤其是香山“以每年五月初五为陈临祭祀日,设坛祭拜,吃粽子,赛龙舟,以纪念陈临。”南北朝史学家魏收以《午日咏岭外风土》记录这一习俗:“麦凉殊未毕,凋鸟早欲闻。喧林尚黄鸟,浮天己白云。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因想苍梧郡,兹日祀陈君。”上述的记载还原了端午节最原始的初衷与愿望就是祀祭先贤,祈求避灾消祸。这就是端午节的由来。
据屈大均《广东新语》云,端午节纪念香山(今中山)人陈临的习俗延续到明朝。也许广东人太低调,不擅宣传,明期以后千载先贤陈临却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甚至连他家乡广东中山绝大多数人只知屈原,不知陈临。我曾有诗感怀:
沧桑世亊见风云,千载高贤数几人。
起落浮沉唯叹息,功成自是有前因。

曾哺育和滋养了沿河而居老百姓的九曲河,穿越了千年风雨,是一条颇有诗情画意的河,是一条有很多故事的河。但时过境迁,斗转星移,这些美好景象,一夜之间就抹平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地政府以九曲河污染严重、河道变窄为由,用钢筋水泥把它全部覆盖了。从此,承载着中山人不少历史文化的九曲河消逝于世人的眼中了!
世间许多事物,要一段距离或时间才看明白。或许当地政府至今才理解错失,感到痛惜。如今惟有通过一些街名,如“上河泊、中河泊、下河泊、河边街、水关街、水楼街”等“带水”的街巷,去追忆那条载着无数风情的九曲河。
现在每经过九曲河遗址,我都会想起昔日的九曲河,那澄碧的溪水和那不清不浊的河水,无时不在我心中激荡。真的,盼望那令人魂牵梦绕的九曲河重新复活,再现清风徐来,碧波荡漾的景象。但,我知道,或许会有这一天的到来;不过,真的恢复了,也没有可能复原当时的风情风貌。所以说,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珍惜当下吧!最后依《天净沙》曲牌填词一首归结全篇:
一河两岸飞花,
小桥曲水人家。
往事前尘若梦,
人间变幻,
起落犹似烟霞。

作者简介:欧阳小华,又名欧阳少桦。中山市火炬区大岭村人。网名,我心飞扬。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历史文学《香山魂》等。
(文棚以散文为主的共享平台,面向全球华人开放,供作者、读者转发和欣赏、交流。“写手”栏目面向全国征集好稿。凡“写手”栏目发表的稿件,当月阅读量达到1万次,编辑部打赏50元;达到2万次,编辑部打赏100元;达到3万次,编辑部打赏150元。请一投一稿, 并注明文体。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文责自负。文章观点不代表本报。非签约作家请注明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全称、账号。)
◆中山日报报业集团新媒体中心
◆编辑:徐向东
◆二审:蓝运良
◆三审:岳才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