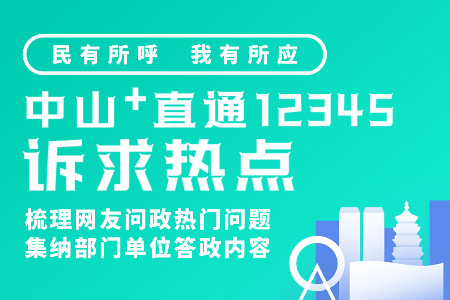自然景观中的诗意对话与哲思探微
诗人黄廉捷的作品时常见诸各大纯文学刊物,每当偶然读到他的诗作,总会让我联想到他的《穿行》等诗集。甲辰年七月二十四日,我在《珠海特区报》“湾韵副刊”上又读到了他的组诗《南方的夏》。加之我近几个月在《澳门日报》“文化镜海”副刊中也屡次品读到他的诗作,这让我更加留意到,他诗的“自然景观”不仅仅是对美的记述,更是对自然、世界触觉的敏锐把握,及对自然与生命本质的深刻反思。
一、自然景观的诗意呈现
黄廉捷的诗歌充满了对自然景观的细致描写,将南方的独特风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远处》中,诗人描绘了雪与草木、大地与阳光的互动,形成了一幅静谧而美丽的画面:“雪敲打复苏的草木 / 空旷的田野吹着口哨 / 大地温柔”。诗中的雪、草木、阳光、山风、白雪和崖石,看似是自然元素的罗列,其实这些元素通过诗人的笔触赋予了生命力。诗中的“大地温柔”和“阳光站起来”,将自然界的温柔与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诗人通过对自然的描绘,传达出对生命力的赞美和对自然循环的敬畏,不仅展示了自然的美,更透过自然景观传达出一种宁静与和谐的感觉。这些诗句,让人联想到约翰·济慈的名句:“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通过对自然美景的描绘,诗人将读者带入一种审美体验,同时也引发了对生命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在《密语》一诗中,诗人探索了内心世界的深层次动态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诗中开头的“光线带着生气裹住密语”,象征着外界因素和内在情感的密切交织,这种描述不仅增添了诗句的神秘性,也深化了我们对情感表达方式的理解。此外,诗中的“内心伤痛沉到河底找到缺失部分”和“记忆的片断把新的活法抛弃”,反映了个体对过去的追忆和对未来不安的心理状态。《密语》通过这种对比和并置,展现了诗人对于个人与环境、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深刻洞察。它不仅补充了黄廉捷作品中对自然和生命主题的探讨,还加深了我们对其对个人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关系的理解,表明诗人在揭示人类生存状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方面具有独到见解。再看《长度》一诗,诗人继续这一探讨,通过河流的隐喻,描绘生命的流动性和不断的变迁,正如“奔向大海只是一种可能,只要土地肥沃——终点只是一个秘密”,表达了对未知未来的接受和对当前生活的珍惜;而诗句“河流有金色的光滋润熟悉的长度”和“把春夏秋冬连接起来,时间就存其底部”,显示了诗人对自然周期和生命循环的深刻认知与尊重。这些诗句不仅加深了读者对诗句中自然与生命交织主题的理解,也丰富了读者对诗中情感和哲学深度的感受。
在《南方的夏》中,黄廉捷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南方独特的自然景观:“灌木丛的鸟撑着小船而来 / 草根热烈倾吐轻薄的气息 / 泥地在练习生长愿望 / 这里的世界被意外燃烧”。这种描写既展现了南方自然的美丽,引导读者进入一个充满诗意的世界,感受自然的魅力与生命的哲思。诗人继续写道:“风来,让野蜂得救 / 大地在喘息中四处寻找雨水 // 火烤的命运把完整的黑暗埋下 / 一把小扇能扇出天南地北高谈阔论 / 有什么在消逝?没有灵魂考究 / 风来,只是沙沙作响的等待”这种反思与现代生态哲学家的观点相呼应。美国生态哲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中写道:“我们必须将自然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仅仅利用的资源。”黄廉捷通过对自然景观的描绘,提醒读者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呼吁人们尊重和保护自然。
此类诗作不仅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在西方文学中找到共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其诗作《咏水仙》(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中写道:“我独自漫游,如同一片浮云 / 在山谷和丘陵间四处漂泊。”华兹华斯通过描绘自然景观,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可见,黄廉捷在《南方的夏》中的诗意描绘和哲学思考,与华兹华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二、生命哲学的隐喻表达
诗人善于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细腻描绘,深入探讨生命的哲学命题,呈现出他对生命本质与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思索。二〇二四年,诗人在《澳门日报》“文化镜海”副刊上发表的两首诗作《闻稻香》(四月三日)与《为人类祝福》(十月十六日),均以独特的隐喻表达了对生命哲学的感悟。其诗作的内在意涵,能够从现象学与生命哲学的角度进行深入解读,揭示出更为丰富的哲理深意。两首诗具体表现为:
(一)生命轮回的哲思。《闻稻香》一诗通过对稻田的描绘,展现生命的四季更迭和丰盈的存在状态。诗中描述,“必须为这里添上酒杯、茶盏、碗碟,还有—— / 丝丝缕缕的春光 / 因为筷子不可缺少伴侣 / 如海富路的秧苗离不开溪水 / 秋冬之时,稻田将绿色封藏”。稻田中的筷子与茶盏、春光与秧苗,这些物象不仅承载着生命的滋养与延续,也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紧密关联。这种关联正如德国现象学家海德格尔所探讨的“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人类的存在总是在自然的怀抱中展开,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更迭无不映射出生命的暂时性与连续性。当诗中提到“稻田将绿色封藏”,我们可以联想到海德格尔对“存有”的解释:万物的存在并不总是显现,而是时隐时现,等待时机去呈现和展开。稻田的“青黄”转变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生命的隐喻,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生命本质在时间中展开,而个体只有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才能真正体验存在的深度。”此外,诗人笔下的“拖拉机摇头晃脑打探来年消息”具有一种对于未来的展望与焦虑。这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绵延”概念密切相关。柏格森强调:生命是持续的流动与创造,像拖拉机般探知未来的期待正是生命绵延的象征。可见,稻田不仅仅是农作物的栖息地,更是生命力延续的场所,代表着希望与未来。
(二)人类的孤独与超越。相比《闻稻香》的自然情感流露,《为人类祝福》则带有更强的哲理色彩,关注人类在广阔自然面前的孤独与超越。这首诗通过“沙子的母亲”“雪山”和“天际之月”的意象,呈现了生命的孤独感与超脱感。月亮作为孤独的象征,与太阳形成对比,它不仅缓解了热烈带来的焦灼,也为人类带来了宁静的慰藉。这种孤独感与尼采的“超人”思想相呼应——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无情与广袤时,不仅要承受孤独,更要在孤独中超越自我,寻找生命的意义。雪山和沙堆之间的距离,既是自然的隔绝,也是人类心灵与精神的分裂。沙堆无法容纳遥远的雪山,这种无力感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荒谬”观念一致。萨特认为,“人的存在是一种没有预设意义的荒谬状态,而人类必须在这无意义的世界中自行赋予意义。”诗中“雪山如此遥远”的意象,正是对人类难以触及的终极目标的象征,但同时,月亮却在“天际”给予了象征性的解脱。诗的最后,“天际月亮,望见地上的自己”,这一幕可以理解为人与宇宙的互映——生命的孤独感在超越自我时得以慰藉和解放。正如西方生命哲学中的悲悯和超脱理念,人类虽渺小如尘土,但在无尽宇宙中依然能反思和追寻自我,从而为人类自身祝福。
生命哲学的隐喻表达诗作仍有一些代表作。试读《沉香》一诗,诗人借沉香的燃烧与转化来探讨生命的变化与成长:“身体被火燃烧后 / 惊动另一种生命 / 传说中的雷火 / 创造了血液中的光泽”。又如诗作《湖边》,呈现了诗人对自然景观深刻的情感投射和对人生经验的哲思。此诗通过湖水这一元素,象征性地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现实的沉思。譬如,诗句“这里的水能盛满往事 / 长在水中的鸣叫描述出更多的安定”,揭示内心的一种渴望;而诗句“杂乱的人间有画写的墓碑 / 尘世吹出的泡泡能赢得无声的宠幸”,则反映了诗人对人类社会的混沌和生命脆弱性的感慨;再读诗句“湖中鸣叫不断 / 裂变的地方将整个往事剔掉”,则似乎在说,自然界的持续声响和变化有着洗涤心灵,去除往事痕迹的力量。可以说,以上这种对生命变化的描写充满了隐喻,暗示着生命在经历痛苦与考验后,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和活力。
这种哲思让人不禁联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名言:“火是万物的源头”("Fire is the origin of all things")。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万物处于不断变化和流转中,火象征着这种变化的本质。诗人黄廉捷通过沉香的燃烧与重生,巧妙地展现了这一哲学观念,体现出生命在磨难中重生的可能性。此外,这种对生命哲学的探讨也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思想相呼应。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其著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中提出,存在本身即是一种在时间中的展开和变化。诗人通过自然现象的隐喻,表达了生命在时光流转中的成长与转变,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动态理解不谋而合。而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庄子的思想中,变化是生命的本质,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万物都是变化的呈现。
黄廉捷通过沉香的象征,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探讨了生命在变化中的坚韧与美丽。诗人在诸多作品中,善于借用自然景物和历史记忆,以隐喻表达了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不论是《闻稻香》通过稻田的意象诠释了生命的流动与希望,还是《为人类祝福》通过孤独与自然的对比,都探讨人类在广袤天地中的存在与超越。这些作品的隐喻,不仅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更是一种哲学思索,启发读者从海德格尔、柏格森和尼采等哲学家的观点为背景,诗人黄廉捷的作品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找到了生命的韵律,通过细腻的自然描绘和深刻的哲理思考呈现。
三、人与自然的诗意对话
黄廉捷的诗歌不仅描绘了自然景观,还深刻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南方的夏》中,诗人通过描写鸟、草根、泥地等自然元素,揭示了自然的活力与人类活动的互动:“灌木丛的鸟撑着小船而来 / 草根热烈倾吐轻薄的气息 / 泥地在练习生长愿望 / 这里的世界被意外燃烧”。这些描写展示了自然界的生机与活力,也体现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互动。再读《湖边》一诗,诗人对自然界的描绘,“这里的水能盛满往事”和“长在水中的鸣叫描述出更多的安定”,不仅展现湖水的宁静与深邃,也反映湖水作为自然记忆的载体。诗中的“水墨画一般独白”和“暮色之下人群簇拥”,则描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自然美景对人心灵的慰藉作用。
然而,这种和谐并非总是存在。在《偶见村中门牌号》中,诗人通过描述一个与往昔截然不同的村庄,表达了对人类活动对自然与传统影响的反思:“一个与秧苗无关的村名 / 光总从山顶悄然而来 / 混沌的往事已不重要”。这不仅反映了时代变迁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冲击,也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自然与人性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诗人这样描述:“我不想破坏这里的宁静 / 尘世让我学会失明失聪”,反映了诗人对现代社会喧嚣的疏离感和对自然宁静的向往。诗人通过“难于预测的事物在消失 / 像翻书本一页页而过”和“多年不见,世事渐变 / 我已是何许人也”,表达了对时间流逝和世事变迁的感慨。同样,《密语》一诗也得以体现,诗中的“光线带着生气裹住密语 / 内心伤痛沉到河底找到缺失部分”,揭示了个体在现代社会中对传统的怀旧与对现实的不安。尤其是诗句“高跟鞋、牛仔服、汽车搅拌的漂浮物 / 陷入更为现实之景”,生动描绘现代生活元素与传统生活方式的交织和对话。
这种思考与美国自然保护主义者约翰·缪尔(John Muir)的思想相呼应。缪尔在他的著作中强调,自然具有内在的价值,人类应尊重并保护自然,而不是无休止地开发和破坏。在他的作品《我们的国家公园》(Our National Parks)中,他写道:“从任何人的角度看,山脉的高贵之美都应是我们一生中的主旋律”。缪尔的自然保护思想反映了对自然价值的深刻认识,这与诗人黄廉捷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思考不谋而合。而在中国文学中,陶渊明也以其田园诗歌表达了对自然的热爱与向往。他在《归园田居》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通过描绘田园生活的美好,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状态。黄廉捷的诗作在反思现代化对自然的影响时,也传达出对这种和谐的向往。
人与自然,需要诗意的对话,而诗歌恰好是较佳形式。诗人通过《偶见村中门牌号》以及《南方的夏》和《长度》等诗作的记述,不仅是对自然美的追求,更是诗人对世界的敏感触觉和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同时也提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应当追求的和谐共存之道。
为此,黄廉捷的诗歌还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与矛盾。在《偶见村中门牌号》中,诗人通过描写现代化村庄的变化,揭示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破坏。这种对现代化的反思,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思想相呼应。布莱克在其诗作《耶路撒冷》(Jerusalem)中写道:“我不会停止心智战斗,也不会让剑在我手中睡去,直到我们建立新耶路撒冷在英格兰的绿色宜居之地。”布莱克通过诗歌表达了对工业革命对自然破坏的批判,以及对恢复人与自然和谐的呼唤。
好诗总给激起人的想象,好诗总会令人回味。黄廉捷通过对自然景观的细腻描绘和对人类活动的深刻反思,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诗意对话。这些诗作,深刻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哲学思考,更是诗人对世界、人生的理解和经验描绘,一定程度上会引发读者对自然与生命的深层次思考。
作者简介:
郭道荣,笔名:步缘,博士,广东湛江人,高校教师。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500字以内,欢迎短文,可配图,图片必须原创。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方嘉雯 二审 周振捷 三审 黄廉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