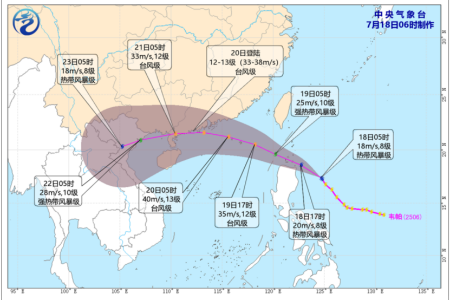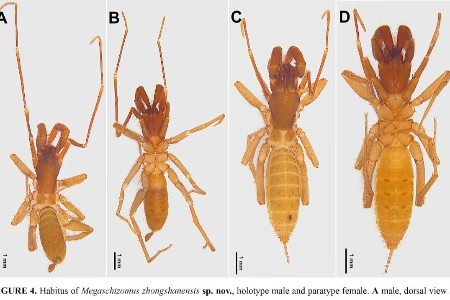“半边云水半边田,对岸河堤对岸村,扯起白帆耕大海,筑起石堤隔开天……”如果你来到中山南部的一个小镇,听到一首首咸水歌在沙田埂间传唱,你一定来到了坦洲。
一条宽阔的长河静静地流淌,河有两岸,这头住着人家,对岸围着沙田。印象中,爷爷家就枕在河边。河堤旁搭了个茅寮,祖屋是村里比较古老的土楼之一。院里有棵龙眼树,一到春季,果树吐蕊开花,一簇簇黄花,挂满枝头。屋后一方寸地用以种菜培瓜,给瓜扎架,给菜施肥,爷爷像照顾自家孩子一样照料着这片田地。
爷爷和新合村里的很多老人一样,每天不是耕田就是捕鱼,手脚天天和水、泥打交道,久而久之满是褶皱皲裂,指甲缝里藏着污泥,怎么洗也洗不干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年年水咸,食水要担,路烂难行,踢跛脚趾公,磨损脚跟。”以前,出门就是泥路,坑坑洼洼,一到雨天就泥泞湿滑。肩上挑着水埕时更要小心,若不是光脚用五个脚趾钳住泥巴走路,就会摔个四脚朝天。沧海桑田,只有脚上沾着泥土,才能沉淀对土地的真情。
渔村人向海而生,因海而兴。对于大海,始终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大冲口渔港常年停泊着一排排渔船。这些木船船篷低矮,船身狭小。船板上铺以草席,可坐可卧。船上随意堆放着虾笼、鱼罩和螃蟹锤,看似破旧简陋,却很实用。
小时候,我最向往的就是泛艇河上,沿着江河捞鱼。爷爷把缯网往空中用力一挥,渔网便铺散开来,而后沉入水中。只要时机一到,就迅速拉紧手绳,缩网收鱼。要是累了就把竹篙插进河底,整饬休息。渔民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唱唱咸水歌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鱼肉鲜嫩,趁着新鲜可以清蒸,或者腌后晒成鱼干。咸鱼白菜,可以吃很饱,也可以吃很久。
后来,我随父母到城里读书。龙眼熟了,爷爷就会进城。金斗湾怡乐园有个水上舞台,当时常有名角来这里表演咸水歌。很多人慕名而来,不仅老年人喜欢,年轻人也听得津津有味。听得多了,也就能吟上一两句。 “妹啊咧,筷子一双同妹拍档,妹呀两人拍档好商量。”“哥啊咧,山顶种葵葵合扇,哥啊咧共哥携手万千年。”爷爷告诉我,那个年代,你一句我一句,姻缘就是这么唱出来的。人有情,歌亦传情。有情之乐,才能唱进人的心坎里。
伴随着江面泛起的层层涟漪,机动渡船向泰丰渡口驶来。我跟随人群踏上了渡船,不一会儿就到了对岸。十年如一日,这艘渡船,把村里的人送出去,把外面的人接回家。
“半边云水半边田,对岸河堤对岸村,扯起白帆耕大海,筑起石堤隔开天……”此刻,熟悉的旋律萦绕在村里的小学,稚嫩的童声唱出了坦洲人的坚强、智慧和质朴。咸水歌扎根在乡间,活跃在乡间。我们能做的,不仅仅是为乡村群众唱几首歌,更重要的是播洒传承和创新的种子。只有这样,这些承载着数代坦洲人记忆的咸水歌才能留得住、传得开、唱得响。
(作者:吴佩俞)

“品忆香山”主题征文活动正在进行中
欢迎进入“中山+”首页投稿
编辑 唐益 二审 张鹏 三审 陈浩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