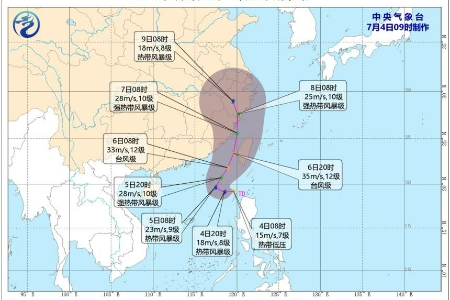六月的风穿街走巷,从宋人的诗里吹来的,带着一点草木气,也带着一身潮州的湿润与温情。
府城茶馆是潮州城里一道不张扬的风景。它不新不闹也不亮,像一个年岁已高却精神安稳的老人,话不多却总让人愿意坐下来听他说说往事。乌檀木的梁柱色泽沉稳,旧桌几上茶渍斑驳,袅袅茶烟升起时,光线就柔了一层。
墙上挂着几幅行草书法,旁边还配着几张老脸谱,红的烈,黑的沉,像是戏台子后刚卸妆没多久的角色,还带着点汗气与人情味。那一墙的墨迹与色彩不是摆设,更像是茶馆与老街一同过日子留下的印记,有烟火气也有旧时光留下的温度。
灯光略暗,茶汤正好。一盏陈年凤凰茶氤氲其间,香气浮动如水雾。我说不清是先听到筝声,还是先看到谜面,总之,它们像两条不约而同的线,正慢慢将我这颗疲惫的心缝合。
那夜的“猜谜选曲”,人聚得满。没有刻意的宣传,没有铺张的背景布,只有一张张靠得很近的木桌,和茶烟后朦朦的眼神。
第一则谜面是:“又逢五一来歌唱。”说是谜,其实像句随口的叙事诗,简简单单。茶馆里沉了一小会儿,有人笑着说:“重六调。”答得不紧不慢,声音像喝完一口老茶后的余温。
这谜底刚落,就有一位乐师上场了,一身月白色长衫,怀里抱着一张旧筝,手指一抬,《问卜》便从琴弦中流出。琴音像春天里第一声鸟鸣,轻巧地落在每个人心头。没有背景音响,也没有灯光变幻,只有人安静地听,耳边是一段调子,心里却是各自的浮沉。
想起小时候,黄昏时分常常在街口的老屋前,听辜伯伯弹筝。他是那种不多话的人,指尖却比话还要灵光。手指节骨分明,指甲修得整整齐齐,筝放在膝上一搭,就像天生为他准备的。那时我年纪小,不懂曲名,只记得每当他开始弹,邻里的声响仿佛都轻了下去,连风都绕着走。
他说,筝不能只弹给人听,也要弹给天听。我那时听不懂,觉得是老人家的浪漫话。可那天在府城茶馆,听见《问卜》的头几个音落下时,我忽然就懂了他说的“天”,也许就是我们心里最不肯说出口的那一方天地。
后来出了道谜:“集芙蓉以为裳。”一听这句,我心里便轻轻一动,芙蓉作裳,不就是那曲《穿花》?果然,一位年轻的女乐手答出之后,便上场与另一人合奏。双筝对弹,调的是轻六,一东一西,两边响起丝丝缕缕的琴音,像两只蝴蝶在茶烟里穿花绕叶,落在茶盏边,落在眼睫上。没人敢大声说话,怕一张口,这蝶就飞了。
那曲之后,有人悄悄拍手,也有人只是闭着眼,轻轻叹了口气。我低头望着茶杯,茶汤早凉,却舍不得喝。那刻的我仿佛不是坐在茶馆,而是坐在那段回不去的青春边上,听着从前没听懂的曲子,心里慢慢有了懂的意思。
到了尾声,茶馆里静得能听见筝弦余音在木梁间游走。这时,潮州灯谜协会的会长缓步上前,随兴而发,作下一则新谜:“怀拥经卷上高阁。”话音刚落,四座已静。
这是场上的第十道谜,也是最难的一道。无人答语,却不是不解,而是舍不得贸然破这意境。那句谜语像一道远山的轮廓,虚实相生,若即若离,叫人心生敬畏。
人群之中,有人低声念叨,有人默默凝思。直到那一刻,潮州筝学会的会长抱着一张百年老筝步上台来,众人心中已隐隐明了,那谜底,是《挨书登楼》。他坐定,指一拨,《挨书登楼》的调子便悠悠升起。
那不是一首简单的曲子,它像一段漫长的独行,从旧楼缓缓登上去,一层一层,每一个音都像踩着书页的声音。楼是高的,书是厚的,人却不慌不急,只是一步一声,一声一意。
我听着,眼眶竟有些热。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想念,一种在某处读书、登楼、独处的日子突然回头的酸楚。那曲子里什么都没说,却什么都有。
曲终,先生起身,茶馆里响起了连绵不绝的掌声。风穿过窗棂,榕树影在地上映照出了一个慢慢伸展的身影,是谁在离去,又是谁刚刚归来。
那晚我走出茶馆,街灯昏黄,榕叶在风中轻轻抖,脚下是潮州的石板路,一块块踩得很实在。我回头看了看茶馆,那灯笼还亮着,像一盏心灯,替人守着过去,也照着将来。
有时候我想,这样的“猜谜选曲”,是把那些被风吹散的日子,一点点收回来。曲子给懂的人听,谜语留给愿意猜的人。真正动人的,从来不是谜底,而是你在猜它的时候,心里忽然亮起来的一盏灯。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500字以内,欢迎短文,可配图,图片必须原创。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方嘉雯 二审 周振捷 三审 黄廉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