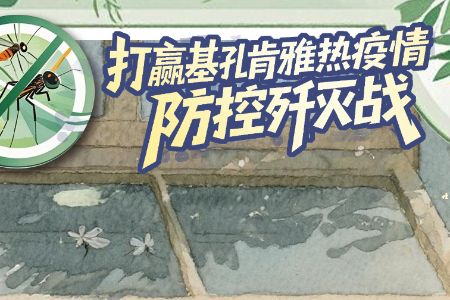桑果铺成满地诗
“情怀已酿深深紫,未品酸甜尽可知。”古诗中所写这种桑果,正是我童年时最喜欢吃的一种野果,我们那里叫桑椹。每当回味起这种美味,我的眼前恍惚出现了家乡的桑树坪,那一大片碧绿如茵的桑树,一颗颗桑椹密密匝匝掩于碧绿的叶片下,清风顺着田野小径吹拂过来,那参差红紫的小小果实,就会微微露出芳容,在记忆深处随风轻轻摇曳,一缕幽幽的清甜滋味便像露珠一般滚动于记忆的味蕾上。
桑椹与杜梨、酸枣,并称为乡村三大野珍。在我乡居的那个年代,曾经是乡村孩子们夏秋两季最好的零食。杜梨不太软绵时,有一种生涩的味道,吃完舌苔发涩,那滋味不太好受。酸枣酸甜爽口,秋天去山里拾捡柴禾或者找猪草的孩子,总有办法摘到一兜一兜的酸枣,那种酸甜滋味,极诱人食欲。不过酸枣吃多了,会胀肚、倒牙,牙齿变得又木又钝又酸,老木头似的,连软和的面条也咬不动。
相比杜梨和酸枣,桑椹就是野珍中的极品,味甜,爽口,鲜红的,老紫的,都好吃,都甜,但甜与甜又是不一样的滋味。鲜红的淡嫩、新鲜,老紫的肥肥胖胖,像紫色的蚕卧在高高的枝头,含在嘴里是一种浓浓的香甜,如蜜,却又不似蜜那般发腻。有经验的孩子,钻进桑林里,都眼疾手快地去摘那肥胖老紫的桑椹,一吃一个乌嘴子,也不刻意去擦掉,带着一张乌嘴子满世界疯玩,仿佛获得了战利品似的。
桑树坪里的桑树隶属于县蚕种场,蚕种场养出来的蚕茧要送到缫丝厂。缫丝厂和蚕种场最兴盛那会儿,经常雇佣附近的妇女去桑树坪里采桑叶。母亲刚进城,听说采摘桑叶可以赚钱贴补家用,乐不可支地加入了采桑叶行列。母亲手法快,采桑叶时舍不得歇一会儿,因此每次收工交桑叶时,都是采得最多的。领到工钱后,母亲就会买肉给我们改善伙食。正值盛夏,姐妹们闹着要买时兴的塑料凉鞋,父亲对于这件事很不赞成,他觉得穿布鞋和凉鞋没啥区别。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母亲总是持有一点纵容和宠溺的。母亲便趁下雨天不上工,去了街上的百货门市。记得我的凉鞋是鲜艳的粉红色,二妹的是碧青的嫩绿色,三妹和小妹的一样,都是鹅黄色。那个夏天,四姐妹穿上新凉鞋,愉快地跟着母亲穿梭在桑林间采桑叶,白皙的小手指飞快地将桑叶采摘到麻袋里,望着很快鼓起来的麻袋,我们仿佛看见那一麻袋碧绿的桑叶变成了甜甜的糖果,好看的衣服和鞋子。
那时候放学回家后,等待我们的不是可口的点心和饮料,而是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活。记忆中的夏天,我们放学后必须放下书包,马上去桑林里帮母亲采桑叶。六月的桑林里特别燥热,蜜蜂嗡嗡地绕着树枝飞舞。但是我们一点也不怕热,因为桑林里充满了桑椹清甜诱人的味道。二妹是姐妹中干活最麻利的,她一头扎进桑林,眼疾手快地去摘那黑红如蚕的桑椹,边摘边吃。等我好不容易兜了一手绢要与小妹们分享时,她的嘴唇已叫桑椹的汁液涂染得一片乌黑。我们对望一眼,忍不住大声笑起来。那时候,幸福感来的是那么容易,仿佛就沾在二妹乌黑乌黑的嘴唇上。
后来,缫丝厂不景气,生产出的布匹绸缎都积压在库房里,发不起工资,厂里就给职工发布匹绸缎。这种不良循环,使得茧价大跌,蚕种场养蚕的积极性遭到了极大的挫伤。不久后,桑树不时遭到砍伐,桑树林一天比一天变得稀疏。也不知哪一天,当我放学后又像往常一样跑到桑树坪想采摘桑椹来吃时,发现桑树坪于一夜间变得光秃秃的,连一株桑树也没有了。我惘然若失地在那片空地上站了许久。
之后,这里变成了新城区,银行、学校、广场、酒店、家属楼一栋一栋相继盖起来,连成了片,一派城镇化气象。然而,我们再也吃不到甘甜如蜜的桑椹了,那紫红斑斓的、肥胖如卧蚕的桑椹,只能葳蕤在梦中的桑树枝头。
又见春风化雨时,桑果铺成满地诗。远隔故乡千里之遥,一旦想起桑树坪,我的眼前恍然出现了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绿色桑海,我们和母亲正穿梭其间,伸长胳臂在枝头采桑叶,白皙的手指很快就被桑叶染得绿格莹莹。
逝去的风景,终是不堪回首。所幸还有记忆可以留存那一片茂盛的桑林,只要一念起,家乡那片绝美的风景就能在意念中反复重现,吟读桑果铺成满地诗,便会让我们的味蕾上增添几分生活的诗意。
前几天读济慈的诗,有一首《希腊古瓮颂》中的诗句我特别喜欢,顺手抄录到笔记本上:
等暮年使这一切都凋落,
只有你如旧。
你竟能铺叙
一个如花的故事,比诗还瑰丽。
济慈的诗,是歌颂一只古瓮的,在我今天读来,它仿佛是写给深藏于我记忆深处的桑树坪——那些密密匝匝掩在碧绿丛中紫红参差的桑椹,一如鲜艳的花儿,瑰丽了我少女的梦。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题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徐向东 二审 韦多加 三审 岳才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