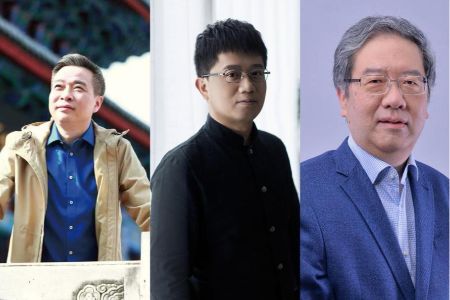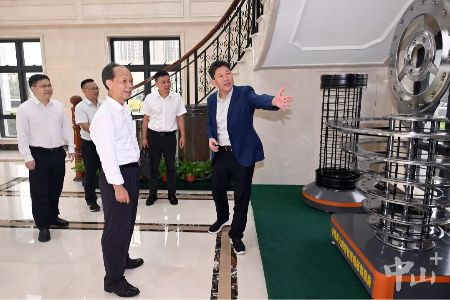乡愁就是一碗面
火苗簌簌作响,坐在灶台上的铁锅里的水已经开了花。
烧开的水花焦急地等待着,它是在等待某一种面下锅。在豫北平原的乡下,一碗面是最接地气的食物,面的种类也很多,烩面、捞面、拉面、挂面、焖面、卤面、刀削面、油泼面、臊子面、砂锅面……
四千年前,先民就掌握了完善的技术,利用面粉做成均匀而细长的面条。有史料记载,吃面吃得热汗淋漓的当属宋朝。汴梁城北食店内有“软羊面”“桐皮面”“冷陶棒子面”等;临安城南食店内有“鸡丝面”“三鲜面”“鹅面”“煎面”等。这一碗从岁月深处走来的面,既观照了历史,又观照了乡愁。
单位门口有一家蓝月亮刀削面,我和几个同事常去造访,去吃面并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饱口福是一种境界,饱眼福是另一种境界。你看师傅,刀不离面,面不离刀,伸直胳膊削面时的场景,正如诗中所言:“一叶落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
杨凌沾水面,那面宽若腰带,第一次吃还闹了笑话。我刚去西安读研时,在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生餐厅,买了一份杨凌沾水面,一大海碗白汤里躺着两片宽若腰带的面,另外给了半小碗臊子,我顺手将臊子倒进了带汤的大海碗中,吃了两口,寡淡无味。这时师弟景涛买饭归来,他是陕西本地人,看了一眼忍不住笑了起来,嘴里连说:“错嘞错嘞,不是这吃法,把面捞出来拌在臊子里才有味儿。”
有一年去河北正定县,面馆里售一种大碗饸饹面。瓷碗大如汤盆,憨厚而壮观,那饸饹面吃进嘴里筋道柔韧,光滑爽口,饸饹汤也是油而不腻,味香浓郁,让人回味悠长。
记忆便在这浓郁的香味中活泛起来,我想起了自己家乡的饸饹面和童年那些遥远的时光。
做饸饹面,需用一个专门的工具及漏床,也称之为轧床。老式河漏床,是一根木头上挖一个水杯粗细的圆洞,上下通透,在圆洞底部钉一块儿扎满小孔的铁皮。河漏床上面有一根圆柱体,链接在一个轴上。轧饸饹面时,把河漏床架在锅上,将和好的面填满圆洞,木柱圆柱体置于洞口,手按住河漏床的把手用力下压,面便从底部的小孔滑入开水锅中。面轧尽后,需要用筷子或者漏勺将漏床底部的面丝切断。
吃饸饹面费时耗力,大的河漏床,需要两三个人共同操作。后来市面上卖一种塑料的简易河漏床,一人即可操作。轧出的面,从外观上看别无二致,一入口立见高下,还是老式河漏床轧出的面筋道。
饸饹面,用料也很讲究,面里加一些榆树皮碾成的面粉,颜色呈土黄色,有的还泛着细微的黑。加入榆树粉是为了增加面的黏性,做出的饸饹面入口滑溜柔软。榆皮粉是将榆树外层皴裂的老皮剔除,留用里层白生生的嫩皮,把嫩皮撕下来在日头下晒干,用碾碾碎再过一遍筛落即可。
如今老式河漏床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若是建一座乡村博物馆,所有和吃面有关的工具、器皿都需要珍藏。珍藏老式河漏床、大瓷碗、长条凳、呼哒呼哒作响的风箱,也珍藏彼时的节气,乡村生活,乡民的悲愁和欢喜,所有的美好和沧桑都值得珍藏。
乡间纯正的面食味道是藏在记忆深处永恒的乡愁。所幸的是,老物件还有一处可睹芳容,在我老家五里外的豆公镇,东街路口有一家饸饹面馆,大敞口的门脸,门口支着一口大铁锅,上面架着一个大河漏床,是一家正宗的榆皮面饸饹馆。每年暑假回老家,我都会跑去品尝,榆面饸饹筋道,滑柔爽口,一入口就能唤起童年的味觉记忆。
作家宁肯曾写过,在国外讲学的日子里,好几天都吃不到面,内心空落落的,后来辗转几条街,终于找到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一碗面下肚才觉得日子过得熨帖。
暮色四合,赶路人裹着一身寒气踅进店中,跺着脚,双手抻到嘴边不停地哈着气,张口点了一碗面,店老板忙着递过来一碗热汤,就去案前做面了。赶路人喝了两口热汤,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他在焦急地等待那一碗面。这时候,再好的美味佳肴、山珍海味,也抵不过一碗承载着乡愁的面。
(不收微信来稿。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徐向东 二审 向才志 三审 岳才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