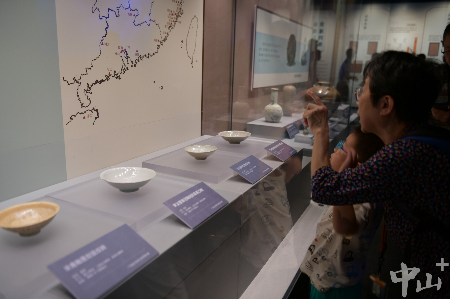地以人贵,人以地传
——浅论香山文化内涵和外延
文化指什么?人文也。而“香山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地域文化。中山市在2016率先提出香山文化概念迄今已有6年。香山文化不仅成为一个全新学术理念,赢得学术界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同,更成为一个区域文化品牌;并且,很有可能成为中山、珠海、澳门三地区域经济文化协同发展的新平台。
日前,在珠海举行的“香山文化内涵和外延”研讨会,不仅体现了当地政府对文化的自觉,而且为构筑这个文化协同发展平台添砖加瓦,善莫大焉。
近六年来,就香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论述可谓高论如云。笔者不想步人后尘,拾人牙慧,但讲同一个主题,内容难免有重复之处。笔者试图以新的视角,从两个方面谈一谈对香山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及个人一些浅见。
首先,所谓香山文化的内涵,就是本土文化。这也是香山文化的根本属性,其囊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是植根于从中原传过来的本土传统文化,“海洋文化”并非一以贯之。
香山本土传统文化的形成,究其原因是“移民”所致。据载,“百越历史上曾历经三大规模移民。一是公元前21年,秦始皇派兵50万南征;二是公元4世纪,西晋的‘八王之乱’导致中原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移;三是南宋末年,皇帝宋端宗携部败走零丁洋沿岸,南宋覆亡,许多宋室及其追随者的后裔流落香山一带。”
前两次与香山关系不大,毕竟香山偏于一隅,太偏远了。史志资料和地质资料表明,直至明代,香山县境还是茫茫大海中的孤岛,遑论是西晋之前。
于香山县来说,人口整体素质得到空前的提高,南宋末年是决定性的历史节点,为日后明清两朝出现人才井喷现象埋下伏笔。所以,笔者拙著《香山魂》以“基因说”去解读这一现象是有确凿的历史依据的。
当年,在骑兵的追逐下,数以十万计的南宋军民且战且退,随宋室辗转流徙香山,并最终在此“覆灭”。可以想像,必然有南宋军民中最勇敢、最具民族气节的精英,尽管最后大部分在崖海之战中阵亡,或者为追兵所捕杀、奴役,但必有一些人倔强地以宋遗民身份在香山存活下来并扎下了根。
这些中原移民,不仅为香山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而且他们的后人把他们的爱国理念与不屈精神继承下来,成为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财富,到了合适时机,就形成人才井喷的现象。
说到香山出现人才井喷现象,许多专家言必称晚清。其实,这种现象,在明朝时已经开始了。史载,仅在明朝嘉靖年间,不足3万人口的香山县产生了16名进士、180名举人。这其中以黄佐最负盛名。《四库全书》认为,在整个明朝的人物中,黄佐的学问最有根底。明末,香山还出了个位高权重的宰相何吾邹,历仕万历至永历六朝,成就他传奇的一生。
需知,明朝长期闭关锁国,实行海禁,所谓的海禁就是不准出海,不准下海,也不能出海进行贸易。所以说,明朝天启年之前,香山文化与所谓的“海洋文化”关系不大,甚至说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且说,蒙元入主中原后,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的记录,人口急剧下降,但往日人烟稀少的香山县,人口没有减少,反而一下子增加了,“有500个姓氏和40个少数民族,有三大语系20种方言,这种现象在全国绝无仅有”。
在中原士子惨受屠戮的情况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亦即中原文化)构成了香山文化的主体,香山人所承传的中华文化精髓尤其可贵。从香山方言中所保留的大量的古汉语词汇与语音,以及民俗习惯就可以一窥全豹。
由于远离政治中心,香山一直保留着古老的中原文化。以习俗为例,除了全国都有的春节、中秋、端午节之外,神仙的节日也不少。如中山沙溪,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这天,吃栾樨饼、舞柴龙,是必备的旧俗;民歌,除了大家熟知的咸水歌之外,在东乡(今中山火炬区)还有流传了几百年的东乡民歌,那首哀怨的长歌《望夫归》最负盛名。粤乐宗师吕文成就是东乡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肖友梅的母亲梁碧帆也是东乡人。在这个音乐沃土的熏陶下,香山产生殿堂级音乐大师最合理不过。
二是从海外传入的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创新文化。
香山县之所以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这与下面的三次历史事件密切相联。因为这样,才开始令到香山县多了一抹“海洋文化”的亮色。
一是古称濠镜澳的澳门被葡占事件。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香山设县伊始,至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完全被葡萄牙所侵占之前,澳门一直隶属香山县管辖。据历代《香山县志》记载,立县之初,香山县设10个乡,澳门隶属于其中的长安乡;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香山县改乡为11个坊都,澳门所属的长安乡改为恭常都;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香山县又改都为9个镇,恭常都分为上恭镇和下恭镇,澳门在地理上属于下恭镇辖区范围。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1572年开始向明朝政府交纳地租,盘踞澳门,1623年(明朝天启三年)更是任命了首任澳门总督。标志着澳门这个小城完全西化,也使得澳门成为中西方经济贸易最先开始的通道。
从此,整个香山地区都处于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中。从政治、法治、宗教到科技等全方位影响着香山。放眼全国,香山人有机会第一时间接触到了西方的理念和西方某些文化。
二是“卖猪仔”事件。在研究香山文化方面,可能许多专家学者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亦即“卖猪仔”对香山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
晚清时期,由于国力衰微,西方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名为“契约华工”,当地人称之为“卖猪仔”。这本来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充满着血与泪。但人的差异性是很大的,一些“猪仔”却和其他人不一样,具有相当强韧性。不仅坚强地活了下来,在异乡安家落户,成为了华侨,有的成为富甲一方的大亨。闻名全国乃至东亚的上海“四大百货 ”公司创始人和大部分股东,全部都是香山人,无一例外不是华侨,兼且创始人和不少股东,就是当年被卖猪仔出去的。
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些猪仔“切换”成华侨后,最早将西方的商业文化带了进来,其路径大抵在家乡和香港崛起,再进驻省会广州,进而移师上海,影响全国。一举成名天下知。
三是“留美幼童”事件。洋务运动以后,清政府先后派了四批共120名学生留美。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被称为“留美幼童”。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也是中国历史上成材率最高,影响最大的学生。
要知道,促成此事的是驻美国总领事官欧阳辉庭和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容闳。他们都是香山县人。因当时满清贵族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出国,所以欧阳辉庭和容闳不得不回乡动员乡亲子弟出国,清廷共派出的百多名学生中,香山县人竟然占了39名。除了官费的还有自费的。这些幼童回国后,大部分在政界、军界、实业界、知识界等多个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比较著名的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体制下的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总办钟文耀,中国铁路之父瞻天佑,著名外交官欧阳庚,中国第一位矿冶工程师吴仰增,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等。除了瞻天佑之外,都是香山人。
以上事件的交织,催生了“华侨群体”“买办群体”“留学生群体”,令香山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催生了一系列新事物新思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启蒙思想家郑观应,旷世伟人孙中山,都是在这样的土壤产生的。
其次,应以“地以人贵,人以地传”诠释香山文化节所蕴含的深刻主题意义,延伸其“外延”。
中国历来有“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正所谓“人杰”方能“地灵”。历史是人创造的,香山因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了许多英才俊彦,产生了众多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应该承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杰出人物推动了历史进步,比如终结帝结、首创共和的孙中山;也应看到,真正令过去的香山人和今日的中山人引以自豪的应该是被誉为世纪伟人的孙中山。
我们应有这个认知,孙中山不仅是中山的,也是珠海和澳门的,也是广东的,全国的,甚至是世界的。所以丘树宏先生提出“孙中山文化”这概念,并且把它上升为国家命题,其意义不仅彰显了孙中山是近代文化之魂。同时,也丰富了香山文化的人文内涵,令香山文化大放异彩。
在香山这块土地,香山不仅诞生像孙中山这么一位大人物,而且产生了一批震古烁今的名人。这本身就是无尽的宝藏,取之不尽的富矿。如何把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和文化发展强势?值得深入探讨。本人有个建议:
一方面,要全面系统梳理香山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正所谓“文以人传,人以文传”,为他们树碑立传,凸显香山的“名人文化”。
就此,本人在六年前已经践行,并且拿出所谓的成果。这成果,就是整整花了我四年的业余时间,用了65万字写就的一部香山历史人物传记——《香山魂》。主要内容撷取香山从南宋到民国的16位有全国影响力名人作为写作对象,并融入深厚的本土文化,从而构筑香山800年的历史文化。拙著在2018年面世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被认为“填补了以文学手法描写中山系列历史名人的空白,活化了中山人文史,塑造了中山名人城市形象。”“是一部期待中的著作”“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至现在止,该书发行了五年了,每年都有政府、银行、工厂等企事业单位批量采购,以作品作礼品赠送嘉宾。当然,这部书也有明显不足,如一些应写进去的人物没有写,今后将不断补充完善,再版发行。
另一方面,中国历来也有“地以人贵,人以地传”之说。必须要保护好名人相关的墓址、故居、村落等。
都说“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好像洞庭湖岳阳楼,因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名扬天下。直到今天,大多数游客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可见,做好历史文化遗存保护,让人们记住故土乡愁多么的重要。
历史遗存是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对重要的历史遗存的保护,不仅仅是单体建筑的保护,也要把周边的环境一同保护下来,这样才有意义。举一个例子,举最近的,在珠海香洲召开研讨会,就举香洲山场村吧。
晚清时期,这里出了一位大名人,叫鲍俊,颇有学识,是被皇帝称誉“书法冠全场”的一位进士。这里有座很有历史价值的古庙,里面留下了不少鲍俊的墨宝。但替之而起的是林立的高楼,等同把古庙包围起来,只留一个出口让村民出入。此等保护是否有意义?
“只重视历史文物本身的保护而忽略了环境的作用的做法不可取。应要意识到,环境是文物古迹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我举一个与此相反的例子,2017年8月,中山市曹边村被国家城乡住建部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被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当年广东省也只有6个村子入选,而中山市只有曹边村获此殊荣。当时我就纳闷,中山还有不少村比之出名百倍,何以偏偏是曹边村集万千骄宠于一身?
直到我来到这个村子,才恍然大悟。曹边村虽离城区仅几公里,但这里仍保留着古村落应有的原始宁静。村落的肌里保护得相当好,至今仍有1000多亩的水田,100多亩的菜地,河沟、板石街、青砖古屋、碉楼,古村应有的元素,曹边村都有。小小的村子,竟有13处市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一砖一瓦都是历史文化,一草一木都是自然之美。在村口的交通要道,有一座碉楼,当地人称炮楼。我环顾四周,只见围绕炮楼土地至少有50亩。据了解,数十年来,村委为了保护好这座炮楼和原有的田园风情,对围绕碉楼数十亩的土地一分不卖。现在,这里成为游客的热闹打卡地。
在香山文化名人的序列中,第一个出场的是梁杞,他是北宋年间的人,宋庆历六年(1046)登进士(广东第一个梁氏进士)。更重要的是,他是香山立县的首倡者。六年前,中山槎桥村民发现了梁杞墓碑。于本土文化而言,这是重大的发现。今年年初,笔者以《守望尘世的故乡》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在文末提议:把梁杞墓定为“中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梁杞墓为依托,规划建设“梁杞纪念公园”,与“树木园”连成一体。或者,直接将“树木园”更名为“梁杞纪念公园”,将香山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深化名人城市的内涵。文章发出后,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重视,有五位政协委员附议写了提案。
最后,笔者想说,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应以高度的历史情怀和文化自觉,积极挖掘三地共同的历史记忆,让“香山文化”这棵参天大树再吐新枝。
(不收微信来稿!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
◆中山日报社媒介拓展中心
◆编辑:徐向东
◆二审:向才志
◆三审:岳才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