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荣之间,永恒转瞬即逝
——读罗筱诗集《这支抒情的芦笛从未停息》
前几天,文友黄祖悦在朋友圈里发了《芦笛声声——罗筱诗集<这支抒情的芦笛从未停息>片段品读》,引来一片赞叹和转发。熟人旧诗得新解,又得十几年岁月加持,绝不是死水又泛起了微澜,而是把陈年好酒装进了新瓶——有心人祖悦做了件让人心生愉悦的痛快事儿。我在微信评论里给祖悦留言:“诗集中尚有《曲线》这样灵巧性感的短诗,供另成一文。”今天难得清闲,在读了一上午阿克梅派,喝了一上午碎银子,吃了一碗五花肉炒鸡蛋黄豆芽粉条当午餐,开了空调准备午睡之后,突然心生一念:那支抒情的芦笛在哪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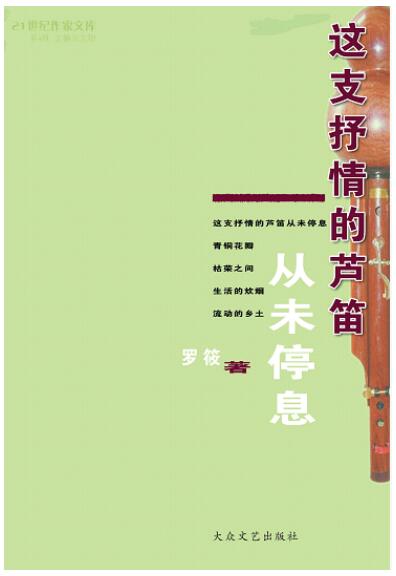
▲罗筱诗集《这支抒情的芦笛从未停息》
事实上,我完全不记得搬家的时候有没有搬过来,搞不好还在旧房子的哪个角落呢。折身就进了书房,居然不费吹灰之力,一眼就看到了它,静悄悄夹在一排诗集中间,像个安静的小媳妇。呵呵,在就好在就好,敢情潜意识里我待这支芦笛还是不薄的呢。
抽出诗集,扉页上芦笛的主人让我“雅正”的签赠还在,字体端庄厚重,无端感觉商周青铜的质地不过如此,只是赠书之人没署名签赠的年月日,而我也已然想不起是在何年月日什么场合。天色阴沉,窗外雷声阵阵,凉风送来夏日难得的清爽,似缪斯授意于我,叫我赶紧起笔,千万不要再给祖悦就灵巧性感的《曲线》们另成一文的机会了。
诗集《这支抒情的芦笛从未停息》(以下简称《芦笛》)第三辑《枯荣之间》约40余首,几乎是清一色的短句,多数五六行,最长不过十二行,最短不过三行。我印象最深的是《曲线》,然后就是《从土到陶》和《枯荣之间》。对《曲线》印象深刻,恐怕跟我是个女人,很在意“曲线”有一点关系,而诗中确实提到了女人的曲线:“鸟飞的痕迹/流水的样子/少年走过的路/‘S’字母/女人的身体/以及谁被它引诱并堕落的过程”。并置的五个形象无一不与曲线相关——鸟、流水、路、字母S、女人,每一句都是实写,每一句都是虚写,从天空到流水,从对飞翔的向往到脚踏实地,从物到人,从少年到女人,从不谙世事到成熟,从美到堕落……这是诗人对曲线深情的抚摸,这更是一个关于追寻、怀想和沉沦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诗人,又何尝不是我们?
短诗的魅力,在于短小而精悍,短小而意味深长,在于打开一个极小的切口,让读者得以遐想切口外面广奥的所指。让我忍不住惊叹的是,罗筱早在我开始写诗的多年之前就已经深谙此道,并且“玩”得漂亮。且看《从土到陶》:“将你打湿/将你柔软/将你镂刻/再将你980度/高温烧烤//好让你/高贵而脆弱地活着”。再看《枯荣之间》:“活着的墙/老去的草/也有些事是草可以而墙不能的//譬如/在秋风中舞蹈”。在诗人眼里,那些短暂、脆弱而卑微的“有生命”的东西,美而易折,他给予这些“有生命”的东西以无限的爱意与怜惜,也给予活着的生命以恣意“舞蹈”的美学意义。
再次翻读《芦笛》,诗人另一首短诗《爱情故事》进入我的聚焦范围:“爱熄灭后/只剩下一壳被烧焦的躯体//许许多多的红嘴鸟/衔着我被风干了的肉/做许许多多的相思巢”,这是诗人的处女作,写于1989年。我打开手机计算器,认真地用2022减去1989,得数是要命的33!很难想象33年前诗人那么年轻,就已经有了如此敏锐的诗歌触角,用如此简单的五行字,处理和平衡爱、死和新生这么重大的命题——放在今天也是可圈可点的。我大学时曾抄写过台湾诗人夏宇的著名短诗《甜蜜的复仇》:“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两相对比,各有千秋:夏胜在意象奇诡,罗胜在意味深长。读者如我,今日联想起来,亦可莞尔。由真正的短诗《爱情故事》顺带说说诗人的非典型“长诗”《想起沈园以及沈园的爱情》。诗人说他没去过沈园,但沈园于他,是一个“适合生长诗、词以及爱情的地方”,是寄存千古诗意的所在,他坦承:“当我老了/诗和酒会成为我生命中的唯一/我将去沈园寻找曾经错过/失落过或者无心伤害过的爱/学会用红豆和黄酒/酿制一生的深情”。
我想每个诗人心中,都安置了一个沈园吧。《钗头凤》二首,我高中就能背诵;而《沈园》二首,则是大学所记,至今也能背诵。罗筱曾说他喜欢一个人旅行,后来我发现这是真的。一个中年的已然发福的男人居然喜欢独自旅行,简直匪夷所思,看来这发福也不是那么中年油腻啊。年轻的时候我倒是真的常常独处,想来其实是实在没有玩伴就故作深沉。但现在,不管去哪儿玩儿我总想身边有个伴儿,起码有个说话和八卦的对象啊。年纪越大,我怎么就越怕孤独呢?这个通常不怎么吭声偶尔一两次喝高了就兴奋得像个毛孩的人,这个当过兵“粗鲁”的发福的中年男,居然喜欢一个人旅行!除了超级闷非我辈所能及,我还能说什么?而他振振有词:一个人在路上,等于让心灵去旅行。只要有心,沿途就有看不够的美景。好吧,这个貌似有道理。但我奉行的是,只要有个可以比较随意说话的、八卦的还算朋友的人在身边,街边摊也不错,一样哪哪儿都是美景。他还解释,有时去的地方比较荒凉,条件简陋,如果有同伴,同伴未必能忍受,况且旅途中吃喝拉撒睡玩等各种鸡毛蒜皮的事,两个人想法不可能完全一致,那就总有一个需要将就另一个,总不那么自由随性,不如一个人潇洒自得。
好吧,这是他罗筱的硬道理。反正我没想过一个人出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我的形象肯定要么像个足金的蠢货,要么像个愤世嫉俗的厌世者,要么就是——我疯了。话虽这么说,但我相信,我们都懂得“泉水清清来自古代的源头/午后我们静坐了片刻/……/一只蝴蝶从我们的心中飞出”(奥德修斯·埃利蒂斯《我们整天在田野行走……》)。是不是人类一敏感起来,一可爱起来,都这副德性?而这德性,是不是每个爱诗的人必须终生携带的,如同食物或者空气?
每个人都是一个多面体,每个诗人的作品从主题到写作风格,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愚钝如我者,重读《芦笛》,要想勾勒出完整的读后印象全貌,哪怕只是个草图,也是困难的、不准确的。我因此愿意抽取《芦笛》中的几首短诗,以期打开一个小切口,描摹我看到的、作者呈现出来的文字的世界、心灵的世界、诗意的世界。
在阅读过程中,我的脑子里经常跳出其他诗人的句子,他们的诗与罗筱的诗,以我的意愿为核心相聚于同一个时空,产生于别人看来十分牵强而于我却十分奇妙的耦合与共振。再举一例。组诗《北方事物》中有一首《落雪》:“大雪 从高处落下/天 卸荷了/负重的大地/却更加轻盈”。怎么味道有那么一点点像韩国诗人高银《瞬间之花》中的短句“下起鹅毛大雪/下起鹅毛大雪/所有人都无罪了”呢?沉浸在阅读中的人,“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而阅读的快感,只有沉浸在阅读中的人才能“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此处低调省略一千字。
我们所寄居的宇宙,万物都在经受时光的磨损。即便是辉煌的文明,都难免湮灭的命运。一颗星与另一颗星的距离,常以光年记录,而当我们仰望星空,那进入我们眼中的星光的发送者,可能早在亿万年就已经死去。啊,这真是让人绝望!渺小平凡的我们,活得多么艰难,“肺炎,痛风,消化不良,肺结核,这些都教我们学会如何死去”(雷·布拉德伯里《夏日永别》),但正因如此,每一刻的活着,好像也可以算作奇迹吧。蜉蝣朝生暮死,何其短暂,但蜉蝣见过晨昏,蜉蝣知道什么是飞翔怎么飞自由,蜉蝣会在死前留下生命的续章,蜉蝣在死后还被我们叹嘘并赋予哲学的怜悯与仰望。枯荣之间,墙头草的“舞蹈”记录了生命之美曾经来过,墙头草以它的短暂以它的柔弱打败要死撑着活很久很久的墙壁——是诗人给墙头草重新命名,是诗人发现墙头草崭新的美学意义,像诗一样好看,不因死而湮灭。
最后必须要絮叨一下诗人的短诗《洞庭湖》。这首诗收录于《诗选刊》2021年第二期,刊出时我读到,惊艳不已,一直以为是诗人近作。今天才发现《芦笛》中已然收录,为组诗《纸上的山水》中的一首,问及罗筱方知这首短诗写于20多年前!二十多年啊,这个中年发福男,今天又给了我岁月从不败美人的一腔艳羡。只是我之前怎么就跟八戒一样囫囵吞枣怎么就选择性眼瞎没看到呢?且硬拉上范仲淹一起放下忧乐,罚抄三遍《洞庭湖》:“挂在长江边上的水袋子/连名字都湿漉漉的/湘 资 沅 澧/日夜往里倒水/水汪汪的大眼睛里/蕴含鱼米之乡/以及麻雀飞过的身影”。那微茫的生命,每一个都在努力与永恒的流逝对抗,在无尽的流逝之上“留下飞过的身影”。如此,转瞬即逝的不是瞬间,而是永恒。至于诗人心中那支抒情的芦笛,是的,它的思考、它的歌唱从未停息。写到这里,窗外雷声依稀还在,万家灯火璀璨,人间无比美好,且容我在永恒的边缘,再炒一碗五花肉炒鸡蛋黄豆芽粉条当晚餐犒劳自己。
(不收微信来稿!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
◆中山日报社媒介拓展中心
◆编辑:徐向东
◆二审:向才志
◆三审:岳才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