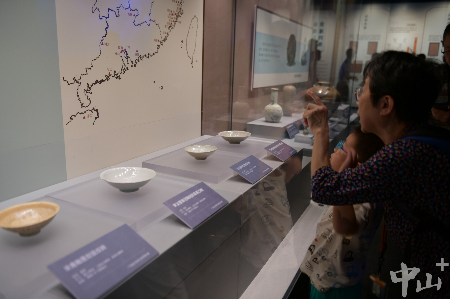小镇与云吞
在小镇生活多年,早已是客舍似家。小镇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腹地,城市拔节的声音带着清鲜的味道,在四围噼哩作响。小镇常住人囗不多,却凭着闲适的田园风景和伟人故里的光环,引得游人如织。
小镇的云吞作为地方特色美食,远近闻名,大小云吞店比比皆是。热汤翻滚,人声鼎沸,饱了眼福,饱了囗福,才称心快意,宾主尽欢。
钟意的云吞店,开在小镇唯一的菜市场附近。朱红色的牌匾上用繁体刻着“凤仪云吞面”,沉静飘逸,毫不招摇。
一间不大的厅堂,两盆叶肥苗壮的文心兰,三四只碗口大的乌龟,在七八张简单的桌凳边择位而栖。
左边透明隔间里,展示着竹升面传统的制作技法。墙上装裱着胡桃木框的直幅中堂,两旁是:“小城小店小生意,食粥食粉食云吞。”中间是大大的“赏面”二字。素雅泛黄的一色裱浸染着年岁的渍团,涉世而来,满面风霜。
有年纪稍长的师傅,着白色的宽松衣衫,跨坐于一根粗壮毛竹之上,在一条窄长的踏板上,单足弹跳。微黄的全蛋面饼,在反复升落的毛竹之下,逐渐被塑出筋骨,抽发灵秀,精壮柔韧。老师傅心眼澄明,恪守本心的植成竹升面,与年俱进的育为云吞皮。
右边大幅玻璃墙内,蒸气缭绕间厨工们手眼疾快。皮与馅在掌心化成群群白鹭,跳入翻滚的热汤,载沉载浮,又颠在捞勺里,细梳毛羽。
收银的店家兼着跑堂,总是目光端定,笑意盈盈。来的多是熟客。街坊旧邻简单寒喧几句,寻位坐定,一碗云吞便上了桌。
汤清如茶,几粒青绿的葱花之下,紧实的鲜肉团透着浅浅的藕粉色,像一条条圆滚滚的金鱼拖着长长的扇尾,憨状可掬,聚首成趣。
捕一只入口,云吞皮滑如绸缎,在口腔游戈自如。轻轻咬开,爽滑酥嫩,鲜汁四溢,肉香满囗。再咬,又有芝麻爆裂的香,像夜空中升腾的烟花,是暗藏的偶遇又必得的惊喜。
呷口清汤,余味悠悠。骨头的香与海味的鲜,在口舌间涌动兴波。
城市轨道、高速快线一条条呼啸着横穿小镇。像赫然的伤疤,带着小镇的骄傲与自卑,慢慢沉潜为奔腾的血脉。
小店消失得很突然。砖石瓦砾,尘灰飞扬。
所有的灯火阑珊处,人潮涌动间,都蓬生着不期而遇和失之交臂。惯看湮灭与更生间积蕴的起与灭,小镇安之若素,不露声色。
很长一段时间,小镇变得精瘦而狭长。四下的风在它嶙峋的骨骼里寂廖地穿行。人们裹紧长衣,匆匆忙忙。小镇踡曲着身体,像捱着严冬的蓓蕾。
某一天,小店的原址上另一家店开张了。名字相近,仍是主营云吞。
大幅落地窗外,十几个花篮长长摆开。店内明晃的吊灯、冷灰色的大理石墙面、临窗的一排高脚凳,时尚又华丽,清冷也疏离。墙上端正的挂着“生意兴隆”的十字绣作。餐牌上的价格涨了一些。奔忙的人之中没有一张相熟的面孔。点了碗云吞,味道已不是从前。
打桩机的轰鸣声在青黄的稻穗间飘摇翻滚,大片的波斯菊正据地为营,其欲逐逐。小镇将温良举在头顶,蜿蜒着挂满正街与偏巷。
偏巷里的重遇像等待的风来。终于声动铎铃,终于盈满长袖。还是那块朱红色的牌匾,依然刻着繁体的“凤仪云吞面”。
店面比从前更小了些。四五张桌子占满了厅堂,依然挂着“赏面”的中堂,下面悬着“楼上工作间,欢迎参观”的字牌。一道细窄的楼梯曲曲折折通上二楼。
老师傅头发沾染着粉面的颜色,他正执着拳头大小的装着粉面的布团,一寸一寸将干粉扑于光滑的面皮上。老师傅动作缓慢,迎风秉烛一般,像轻舟不忍划破水镜,如敬如爱不敢高语。
一旁那根粗壮的毛竹一端缚于绳索,一端魂系山野,它和老师傅一起听惯了南戏,情愁百思,吱吱呀呀几欲开囗。
还是点了碗云吞。入囗入心。
邻桌坐着一对母子。孩子三四岁的样子,眼神明澈,稚声清亮。
“妈妈,这个叫什么呀?”
“云吞啊。”
“妈妈,我们吃的是云吞吗?”
“是云吞,你尝尝看。”
“妈妈,云吞可真好吃!”
行政规划更改了小镇的姓氏,健硕了小镇肱股。小镇的根系在金色的稻田间盘结,小镇的新芽在破与立之中郁郁抽发,那里结满故事,穿越日新月著,包裹在一颗颗云吞里,端给故人与新客。
◆中山日报社媒介拓展中心
◆编辑:徐向东
◆二审:向才志
◆三审:魏礼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