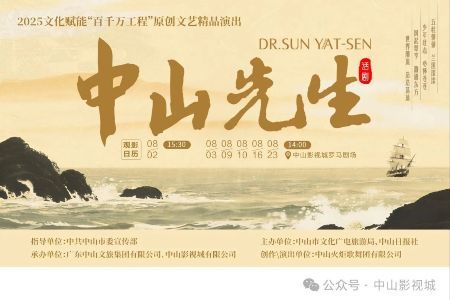走进洗新乡
从重庆市石柱县城出发,驱车40分钟就到了石柱县洗新乡。远处群山叠翠沟壑纵横郁郁葱葱,薄雾缭绕若隐若现宛若仙境;近处葱绿的玉米地里,那些胖嘟嘟的宝宝们正迎风摇曳,三五成群的烟农正收割烟叶,丰收的喜悦洋溢在脸上。

沿着水泥路下行,车轮卷起漫天灰尘。汽车在峡谷中穿行,两岸悬崖峭壁,峡谷深不见底,翠绿满眼清新扑鼻,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让人心旷神怡。
一栋写有“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标语的米黄色大楼提醒我们洗新乡政府到了。街上水泥地面坑洼斑驳,几栋民房紧凑地矗立在街道两旁。“戴口罩 不聚集 疫情防控别放松”,红底白字的标语悬挂在一栋木列房墙上,墙根下晒着油炸木姜子、水煮洋芋片,五六个耄耋老人正闲适地坐在一家小商店门口闲聊,商店货架上稀稀疏疏摆放着方便面、饮料、食用油、香烟等商品。他们好奇地打量我,质朴地调侃:“我们这个乡场不大,没有宾馆没有饭店,划根火柴可以转一圈。不过想吃什么我可以去地里现摘回来给你们煮,家里的床也可以让你们睡。”我的心一下子被拉近了。
抗捐洞
距洗新乡政府2公里林木蓊郁的上盖山杨福湾,一片柳杉林深处,隐藏着一口能容一个人猫腰进入的山洞,当地人叫“抗捐洞”。匍匐进洞爬行三四米,洞内豁然开朗,出现两层楼高2米宽的巷道,往前约50米,分成三条岔道直抵后洞口,洞外悬崖绝壁杂树丛生。
“我们这里还是红色革命老区呢。”一位头戴白纱帽脚穿红凉鞋的婆婆自豪地对我们讲起久远的革命故事。听着先烈故事,我仿佛置身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仿佛看到革命先烈们为了革命事业浴血奋战的场景,想到当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热泪盈眶。
“余先礼烈士现在还有后人吗?”我不禁问道。“有,余先礼还有个儿子名叫余祖吉,今年90岁,住在万寿村沙坝组,享受着国家低保。余祖吉的儿子已去世,孙子在县城打工;老人不幸摔断了腿,由三个女儿轮流照顾。余先礼现在都有重孙辈啦,一大家总共有三十几口人呢。”婆婆朗声回答。
余先礼的曾外孙吕仁荣表示,他们要继承和发扬曾祖父的革命遗志,将他抗捐的故事代代相传。当地政府也准备打造杨福湾“抗捐洞”红色旅游景点,传承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100亩莼菜基地
西晋时期,有个叫张翰的人在洛阳当官。一天秋风乍起,他想起故乡吴中的莼菜、莼羹和鲈鱼,叹曰:“人生贵适志,何能驾官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弃官归里,留下了莼鲈之思的典故。美味的莼菜不仅吴中有,平均海拔1340米的洗新乡万寿村更是其理想家园。
清晨,远处和近处的绿油油的大山笼罩着一层薄雾,忽远忽近,若即若离,像是仙女舞动的轻纱。半山腰层层叠叠的100亩莼菜梯田里,一张张椭圆形嫩绿的叶子浮在水面,像羞怯少女张开的双臂,一朵朵粉红的花蕾探出水面,晶莹滋润、楚楚动人。太阳刚冒红,体格健壮头发乌黑、红色运动衫裤的万寿村副支书赵红军,带领八九个村民高高挽起裤腿站在50厘米左右水深的莼菜田里,面带微笑,勾腰低头,右手在水里熟练地撇开浮叶,顺势将触碰到的水草一把捞起,搭在左手上,然后用三根手指托住嫩叶根部,拇指迅速掐断一把捞出水面,扔进身旁的盆子里……
晚上,驻村队员和村干部一起,对村民采摘的莼菜“杀青”。为了让莼菜受热均匀,他们将莼菜装进一个满是漏眼的不锈钢盆子,放入不锈钢锅里的沸水中,边煮边用水瓢搅拌,待莼菜的叶柄和叶尖变黄变白后,迅速将盆子抬起来,滗掉沸水,倒入盛有山泉水的干净大盆里,将不锈钢筲箕放入盆中,边往盆里注水边舀出从筲箕漏眼里滗出的热水。莼菜冷却后,舀入一个装满山泉水的大水瓮里,浸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剔除杂质和大的叶片后,装瓶带到石柱县城送到消费者手上。
近一个多月来,万寿村驻村队员和村干部一起,想方设法将水中的莼菜变现,共卖出1600多斤16000多元,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为乡村产业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的精神让我深受感动。
千年银杏树
“金樱相亚枝枝袅,银杏低垂颗颗圆。”“古柏高枝银杏实,几千年物到而今。”洗新乡丰田村田坪组,一颗参天古银杏树长在一块宽广的平坝上,地面裸露的根须盘根错节直径约15米。成人游客们惬意地散坐在围绕树根的条石上乘凉,两个白衣女孩用水枪喷出两条蛟龙交互缠绕,另外三个小孩羡慕地看着,跃跃欲试。

树高约50米,高耸入云,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绿巨人。树胸径约2.8米,5个身高1.75米的成人男子刚好合抱。树冠径约13米,整棵树像一把撑开的巨伞,为树下的游人遮住似火骄阳。一颗颗青黄的白果挂在树叶间,一阵大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白果摇摆晃荡,激情合奏一曲美妙的乐章。
当地村民吴先生说,1970年代,重庆市林业局专家先用树木测量生长锥在银杏树主干上钻取样本,再利用树木年轮分析仪进行年轮分析鉴定,最终得出该树的实际年龄约800多年。为了防止雨水或病虫害侵入造成树木腐烂,工作人员取样后对树孔进行消毒,用玻璃胶进行了填充。
“这棵树苍翠挺拔,生机勃勃。”游客们纷纷赞叹,在树下拍照留念。“这棵树很神奇,不仅能预报天气,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呢。”吴先生幽幽地说。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巴盐古道的必经之地。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叫余春的年轻背盐汉子正艰难地行走在巴盐古道上,暴风雨使他迷失了方向,与背盐队走散了。他正心灰意冷,突然发现身后跟着一女子,身子瘦瘦的,穿着一身绿衣裳,自称银杏儿。银杏儿与他温柔相待,如影随形。二人互生情愫,结为伉俪。
银杏儿在家洒扫庭除洗衣做饭,余春继续在巴盐古道走南闯北。一年后,余春背盐归来,发现家里干净整洁,银杏儿却不知道去向。他四处寻找不得,伤心痛哭。一天深夜,银杏儿缓缓入梦来告诉他,她就是路边那棵古银杏树。想起一年来的恩恩爱爱,余春伤心欲绝、万念俱灰。不久他出家为僧,在木鱼声声中,为银杏儿祈福。
这棵银杏树一直守护着村庄,见证了村民生活越来越好。

天生桥
同行的吴先生说,到了丰田村,不去看看天生桥,就等于没来。在他带领下,我们直奔天生桥。
一片茂密的森林深处,一条水泥人行步道自上而下,蜿蜒曲折,我手拄着木棍,小心翼翼沿水泥阶梯下行,路旁的野花张开笑脸鼓励我,树丛中的青蛙时不时跳出来跟我打招呼,同行的小女孩们更是“嬢嬢”“嬢嬢”地问这问那,似乎这原始森林里藏着她们问不完的秘密。
“哇!好大好高的一座石拱桥呀!”同伴的惊呼,将我的视线引向一座横跨在两座山间的“石拱桥”。“真美呀!”我忍不住惊叹。话没落声,只听右膝“嘎嘣”一声脆响,我心里咯噔一下,膝盖又糟了!我的右脚已无法抬起。走在前面的先生心有灵犀似的发现了我的不好,赶紧回头架起我的左肩,用力辅助我下到一个最佳观测点。
这是一座横跨溪涧的小山,由于山水长年累月冲蚀,中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酷似一座天然的拱桥。拱桥跨度约40米,拱高至沟底约80米,拱顶岩石层厚约15米,桥面宽3米多。
天生桥雄伟壮观,气势磅礴,不能不让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拱顶之上,杂树林立,植被葱茏,空气清新。拱桥之下,树木葱翠,鸟语花香,水声潺潺。吴先生又讲起天生桥的传说。
夜幕降临,凉风习习,洗新乡变得一片静谧。
(这是一个共享、互动平台!“文棚”面向全球华人开放,供作者和读者交流、推送。其“写手”栏目向全国征集好稿,凡当月阅读量达6000次,编辑部打赏50元/篇,12000次则打赏100元/篇;另外,每月由文棚主编推荐5篇优秀作品,给予50-100元奖励。优秀作品可以参加季赛和年度总决赛。请一投一稿,并注明文体。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全称、户名、账号等。文责自负,发现造假、抄袭、套改等即予曝光。)
◆中山日报社媒介拓展中心
◆图/作者提供
◆编辑:徐向东 实习生 袁隽清
◆二审:韦多加
◆三审:魏礼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