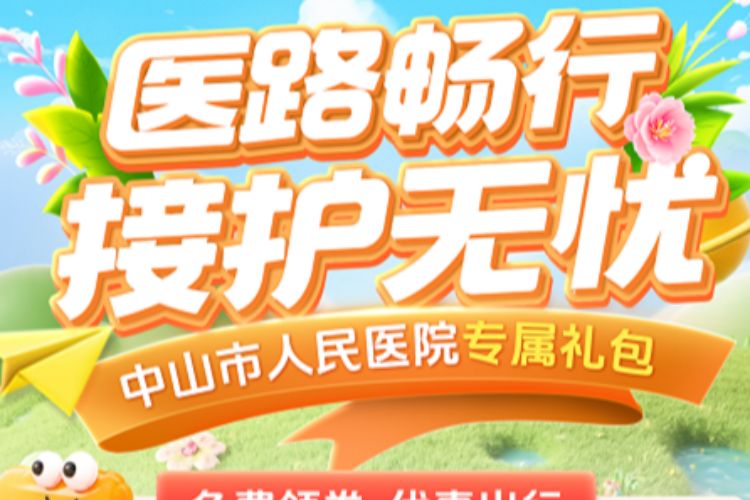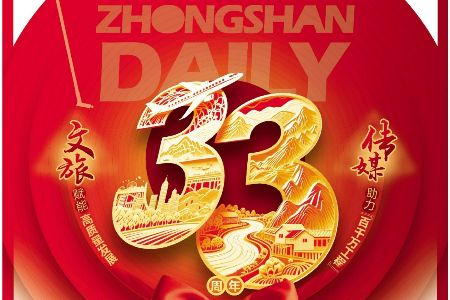舌尖上的潮州鱼生
中秋到,秋风起,天转凉,正是吃鱼生的旺季。夜间好友小聚,茶过五味之后,常常相顾一笑,瞬间便心意相通,于是纷纷起身,一齐吆喝:“食鱼生去!”
这熟悉的一幕,身为潮州人,相信很多人都曾经亲历过。潮州鱼生之所以能够让无数的胃长久惦念,首先得益于其制作工艺的精良,并且对每一个环节都把关极严。譬如从池中捞鱼时,动作要轻柔缓慢,千万不可使鱼儿受惊挣扎,否则肉质就会大打折扣;譬如放血,要求从活鱼的两鳃和尾部动刀,使鲜血全部流出,这样切出来的鱼肉方能洁白如雪,完全呈透明状,成为名副其实的“玻璃肉”。这一过程,稍有不慎,便可导致砸锅。但师傅动作麻利,手法娴熟,只需几分钟,原本还活蹦乱跳的鱼,就不明不白地皮肉分离了。最后,再取下脊背处两片晶莹剔透的鱼肉,在干爽的面巾上抹净,挂于通风处的竹钩上,让寒风一遍遍地抚摩着,使肉质自然抵达食用的最佳状态。这是走火入魔的食经,但鱼生的鲜得要命又恰好证明了所有的这些讲究并非店家的故弄玄虚。
当然,重头戏还是把晾过的鱼片用连刀手法切成薄片的过程,这既要追求切片的神速,又务使鱼生薄如蝉翼,轻可吹起。没有多年如一日的磨炼,是不可能进入纯青之境的。但半根烟的工夫还不到,一片通风透气的圆竹篾片上,便被师傅变戏法般地均匀铺上了一层鱼生,仿佛只是一阵风拂过,篾片上便洒满了花瓣般,让观者无不拍手叫绝。
在这紧要关头,运刀如风的师傅总是一脸专注,他们绝不允许一片不合规格的鱼肉出现在自己的快刀之下。这个时候,我常常觉得鱼生师傅俨然就是古代纵横江湖的刀客,他们不单同样把刀耍得登峰造极出神入化,而且视鱼生刀为其命根子。我曾多次见过一些外地客人出于好奇,趁师傅不备,偷偷操起刀端详起来。这通常会招来师傅的一声呵斥,不单单是为顾客的安全着想,更多的是心疼自己的工具——倘不小心伤了薄如纸的刀刃,这个晚上接下来的生意可就做不成了。
淡水鱼肉质清淡,鱼生尚需佐料加以提味。丰富的配料是潮州鱼生的另一大特色。将蒜片、菜脯、花生、姜丝、萝卜丝、芹菜、香菜、辣椒、金不换、洋葱、杨桃等装成五颜六色的一大盘,原本尖锐对立的各种味道,在鲜嫩滑口的生鱼片的统领与协调下,相互妥协,最终达成了某种和谐。咀嚼着这样的美味,欢愉的味蕾会时刻提醒你,这简直就是神仙才有的享受。
你别小瞧这些配料,每一样可都是师傅心血的结晶。比如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白萝卜丝,就是配料中的一绝,随便拈起一根来,你才会发现均细如发丝。每每筷子伸向这些萝卜丝,心中总会生出一丝怜惜来。切这样的细丝特别费工耗时,只能按份额定量供应,所以要悠着点吃,倘若几筷子便夹完,想再向店主多索一小撮,还得小心地赔着笑脸。
吃鱼生时,每人还需配备一小碗呈金黄色的酱料,这是所有调味品的灵魂,在视觉上就能勾人食欲。我总觉得这碗秘制而成的酱料有着特殊的魔力,它在负责追杀鱼片上残存的最后一丝鱼腥味的同时,更是把鱼生衬托得鲜甜无比,让人一旦想起,那胃早已是迫不及待;一吃香辣甜爽之感即刻充满口腔,教人欲罢不能;而一朝远离,又朝暮思念,即便时间再长久,也无法把这种馋偷走。
关于潮州人吃鱼生,本土还流传着这样一段历史故事。古昔之时,潮州人便有了吃生食的传统,并且对鱼生的原始口感和营养情有独钟,只是潮州的吃法属于生吞活剥一类。公元819年,一代大文豪韩愈被贬潮州,抵潮之后,他也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中原贵族饮食文化带了过来,这才迎来了潮州鱼生的春天。看来饮食也如人情,一样讲究缘分。但是,种田如绣花的潮州人并不满足于只是一味模仿,他们同样把血液里凡事追求极致的秉性倾注在鱼生上。最终,在潮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种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让制作鱼生的工艺得到全方位提升,并且日臻完美,形成鲜明特色。
看来,这一盘鱼生,吃的不只是味道,还是历史、文化,这就难怪有时顺手把鱼生图片转发至朋友圈后,在外打拼的朋友们会纷纷留言,说这是满满的乡愁啊。
潮州每个角落均有吃鱼生的传统,做法也是大同小异,但以官塘鱼生最负盛名。路遇官塘人,他们常常随口就抛一句“有空来官塘食鱼生”,每一个字眼都透着自豪感。为什么官塘鱼生如此出名呢?听老一辈的人说,官塘自古就枕着北溪河,再加上鱼塘遍布,水产丰富,故很早就吃起了鱼生,后来更是一直以潮州鱼生的发源地自居,久而久之,大家也都公认官塘鱼生才是最正宗的潮州鱼生。从前每逢中秋佳节,官塘人还有以鱼生祭拜月娘的民俗,然后男女老少围坐一桌,“举头赏明月,低头食鱼生”,悠然自在,无比惬意。
正是因为官塘鱼生的名气大,我在潮州府城多次见到一些鱼生店挂着“食鱼生何须到官塘”的牌子,以此招徕往来顾客。言下之意,大概是掌刀的师傅都是官塘人,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奔波十几公里的路前往官塘。但一些骨灰级的老食客却不以为然,因为城乡的空气质量本就迥异,在婆雀岭这一屏障的护卫下,官塘更是近乎一个天然氧吧,所以常常让人有“寻常一样池中鱼,才抵官塘便不同”的慨叹,因而这区区十几公里,怎能阻挡吃货们的匆匆步履呢。况且,吃东西也讲究一个氛围,或许只有来官塘,在一阵阵清澈和风中,在一声声昂扬蛙鸣里,远道而来者才能捕捉到享用美食的那种特殊体验,进而使自己的食欲一下子便抵达最佳的状态。热爱美食,表面上看似乎只是物质层面的,而本质上却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精神层面的。
作为地道的官塘人,常有友人咨询我官塘哪家鱼生店最棒。记忆中,官塘的鱼生店一直维持在二十家左右,至于孰优孰劣,这个真是难下定论。食客们的嘴巴最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里,没有一手绝活,哪家店能继续生存下去呢?但是,就口碑而言,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府前街的“老义鱼生”是很多资深食客的最爱。只是店主老义叔脾气古怪,稍微一言不合,就把刀往砧板上一撂,黑着脸说,这生意他不做了,即便是多年熟客,他也不留情面。但奇怪的是,这一点丝毫也不影响他的火爆生意,每每去得迟了,他的池子里便空空如也。
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大概也只有这种生性孤僻的人,才能凡事做到极致,把鱼生的制作工艺推向顶峰罢。而沦陷在他的手艺里而无法自拔的食客们,久而久之,不单对其坏脾气见怪不怪了,甚至还觉得他吹胡子瞪眼的样子特别可爱。如今,老义叔已作古多年,他那柄闪着寒光的鱼生刀或许也早已不见了,但许多人还是念念不忘“老义鱼生”,这真应了“你离开了江湖,江湖上还有你的传说”那句老话。
吃鱼生的过程,同样也有很多地方值得玩味。说来有趣,素来在吃喝上恪守礼仪规矩的潮州人,到了吃鱼生这一环节,却一反常态,把争着抢着当成一种乐趣,并且以此为荣,大有非如此不足以极尽其兴之意,甚至筷子在盘子上面打架的事也偶有发生。这个风卷残云的紧张场面,与喝工夫茶时“请、请、请”的谦让之声不绝于耳恰恰相反。这是因为鱼生刚端上桌面里,品质最为上乘,若是一味推让细嚼慢咽,吃不到一半,鱼肉便开始返潮变软了。正是基于此,大家才跳出常规,放下斯文,大口大口地尽情享用美味。我想,这大概也是生活中潮州人不拘常规、擅长因情势而灵活变通的一个例子吧。但是,豪爽归豪爽,一些礼节却并不因此而有所偏废,譬如盘中最为美味的鱼鳍,一定要献给远客,以示恭敬,这一推一让,让人颇觉古风扑面。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徐向东 二审 韦多加 三审 岳才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