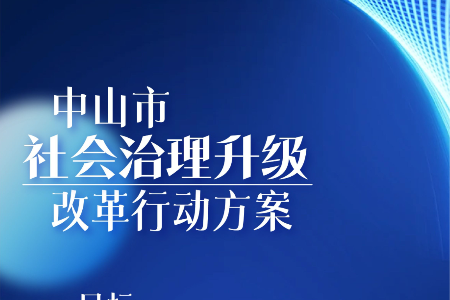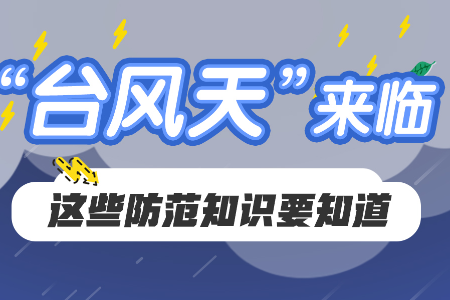午后的阳光穿过竹林,在五桂山街道桂南旗溪村的青石板路上洒下斑驳光影。香草农场旁,一群年轻人支起电脑,把摇曳的香草当作背景,忽而微风起,远处又飘来手冲咖啡的香气,有人盘腿坐在木栈道上,开着视频会议,与蝉鸣合奏,恰似美妙的乐曲……
在旗溪村,总能看见这些背着电脑、穿梭于自然与工作之间的年轻人,他们就是新时代的“数字游民”——不依赖固定办公地点,以互联网为生,追求自由的工作与生活方式。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旗溪村已累计吸引近百名“数字游民”旅居,成为中山颇具代表性的“数字游民”聚集地。

跨界者的乡村实践
作为DNC旗溪数字游民基地主理人,邢晓雯的转型轨迹恰是这群“数字游民”的缩影。从传统媒体调查记者到互联网大厂从业者,从古村保育公益人到出国留学工作体验后又回到中山……10年间,她跨越多重领域的探索,最终于2024年扎根旗溪村。

为什么会选择旗溪?在邢晓雯看来,这里完美契合了“数字游民”对“第三空间”的想象:地理上,旗溪村坐落于大湾区腹地的中山市五桂山自然保护区内,不仅拥有优质的自然生态和清新空气,距离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等城市的车程均不超过90分钟;精神上,这里的生态理念与当下“数字游民”推崇的环保理念及追求的生活品质高度契合。
更重要的是,过去数年间,这里已吸引全国多地高学历或具备特别技能专长的人才定居。这些新村民或在村里实践生态农业种植与产品研发,或在云端工作成为乡村数字游民,或选择在此度过人生“间隔年”,逐渐形成了活跃的高知社群,为“数字游民”社区的打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就这样,邢晓雯与自雇自足品牌创始人刘琼雄在这里租下了村民毛哥家的一栋三层小楼,打造了DNC旗溪数字游民基地,期待它成为世界各地“数字游民”融入乡村的一个连接点,与乡村产生更深度的链接,真正落地乡村扎根发展。

多元群体的精神共鸣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数字游民”选择旗溪,不仅是逃离城市,更是寻找精神共鸣。
Julie是一位资深的“数字游民”,她曾去过浙江安吉的DNA数字游民公社以及海南文昌发起的纯·数字游民共居·办公空间,而现在她来到了旗溪村,打算居住一个月的时间。她表示,相较于其他村子,旗溪村更具年轻化的特质,“这种年轻化不仅体现在村里年轻人多,更体现在这里物价低、生活成本低,业态超前方面,总之就是不太‘村’。”Julie说道。
怪兽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她在“间隔年”来到旗溪村,计划在这里开启创业之路。现在,她和另外四个小伙伴一起主理着“不装商店”。这个五人团队中,每个人都从事不同职业,擅长设计的怪兽负责店面设计和文创设计。她认为,旗溪村紧密的社区网络和互助精神给了她很大启发。“在这里,大家关系融洽,经常一起组织活动。这种没有组织架构、纯粹为了做好一件事的氛围,反而能激发更大的创造力。”怪兽说。

芳芳的经历则展现了另一种“数字游民”的生活状态。曾从事制冷设备工程工作的她,在一次自然教育课程中偶然得知旗溪村,便被这里“多元包容,尊重和支持”的氛围深深吸引。辞职后,她毅然决定加入这个乡村社区,不仅将老宅改造成民宿,还开启了手工皂制作和线上心理咨询的多元生计探索。“在这里,生活的节奏由自己掌控,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与自己内在声音对话的空间。”芳芳说。

“数字游民”带来的乡村变革
“数字游民”的到来,正在悄然改变着旗溪村的生态。据悉,这个常住人口仅250余人的小村庄,如今已吸引了近百名“数字游民”旅居,其中不乏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挪威卑尔根建筑学院等国内外顶尖高校的精英人才。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消费力,更是一股推动乡村变革的新动能。

“单以我们DNC旗溪数字游民基地来说,运营不到一年,已经出现一批‘候鸟式’的‘数字游民’会员,他们会在这里短住几周或一个月,然后去其他“数字游民”社区旅居体验,之后再回来旗溪村,这样就形成了知识共享的良性循环。”晓雯表示,这些高知群体正深度参与乡村治理,亦如近期新村民们自发形成了“旗溪爱树小组”,在村里从事朴门生态设计的小张带领新老村民实地考察和学习保护古树的知识,也为村里环境保护建言献策;在建设“无废乡村”的过程中,新村民又多次自发组织生态议题讨论会。最近,由新老村民发起、相关政府部门指导下的“旗溪共同缔造委员会”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中,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又一创新探索。
事实上,随着“数字游民”的聚集,旗溪村的产业形态也在升级。原本闲置的老宅被改造成特色民宿,废弃的仓库变身文创空间。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些新业态大多采用“线上运营+在地体验”的混合模式,既保留了乡村特色,又接入了全球市场。本地种植的香草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手作工坊的课程被制成短视频吸引国际学员,就连田间地头的会议场景也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流量密码。

这种变革也在2023年获得了系统性支撑。五桂山街道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旗溪村成立了“旗溪创谷”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基地,不仅提供办公空间和政策支持,更搭建起新老村民交流的平台。在这里,“数字游民”的创新思维与传统村落的在地智慧相互碰撞,催生出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
采访最后,芳芳说:“我想象的游民可能更多地在一个‘游’字,但我喜欢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所以我想在这里长久地生活,更想和这里的人建立更深厚的链接。”
编辑 陈家浩 二审 曾淑花 三审 苏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