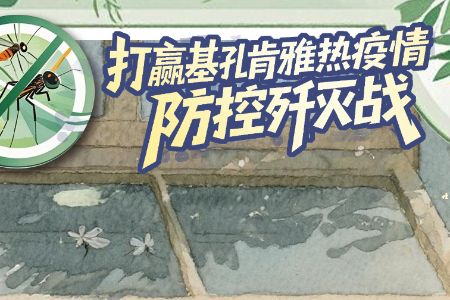由于不在国内,不参加国内任何文学活动,出书较少,张惠雯的名字还少为人知,但低调的姿态仍旧挡不住她独特的写作所散发的迷人魅力。实际上,早在2005年,在余华的推荐之下,她的作品《水晶孩童》就已经亮相国内文坛。十多年里,她像个手艺人一样,在自娱自乐、自我满足的状态下慢工出细活,磨出了不慌不忙带有其整体性的小说集作品《在南方》。

记者:《在南方》书写了中国移民在美国南方的生活与心路历程,连缀成了美国华人移民的南方生活画卷。您认为在南方的生活带给你的创作来了哪些改变?
张惠雯:“异质文化冲击”不是我来美国后发生的,它发生得很早,我17岁到新加坡读大学时就经历了这种冲击。但那时候年纪小,很快就适应了新生活。新加坡是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很多元的城市,所以,也可以说给我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过渡。二十几岁开始写作之前,我的“文学养料”基本都是西方文学,所以我对西方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并不陌生。搬到美国后,新环境让我的视野和写作背景更开阔一些,有更多的人和故事可写。但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生活多年后,我反而更倾向于一种“普世”写法。这并不是说我不在乎不同文化、地域特色,而是说我更着重人性的相通之处。我希望我写的故事无论发生在哪里,其人物都可以穿越任何边界、壁垒,到达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个人心里,使他能从中辨认出自身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去满足他们对异国故事、情调的猎奇心理。
记者:在此次评奖的颁奖词中,评委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几近完美的小说技术,使得她的小说具有教科书般的示范意义,也让她成为令人尊敬的小说家。”您认为小说需要什么技术,这种技术如何才能使之变成小说艺术?
张惠雯:这评价真是太高了,我不得不说在我的虚荣心得到最大满足的同时,我也感到很大的压力。就是说,我觉得我必须写得更好,才配得上这样的赞誉。如果详细谈这些技术,可能要写一篇上万字的论文。简单地说,我的方法是多读经典,我相信小说的技艺只能通过阅读好小说、不断写作获得。我不是那么追求新技法,况且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创新也并不怎么新,是用西方现代文学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用过的写法来写中国故事。我记得博尔赫斯在一篇序言里表达过这个意思(原话我不记得了):通过阅读往昔的灿烂诗篇,去找回文学曾有过的但现已失去的荣光。我想我喜欢的方向就是回头去寻找我们遗失、忽略的那些过去有过的好东西。我在写作时很少去想这篇小说是不是在形式上很新,我考虑的问题首先是它够不够好。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日出每次总能唤醒人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它不需要过多的花样翻新。此外,我觉得重要的还有态度。小说家要尽可能认真对待自己的每篇作品,把它看作一个“文本”而非一个急于表述的故事,必须时时控制自己的表达欲、吸引关注的欲望。这样的话,你会更专注于“风格”这件事,更耐心地打磨每个词、每个句式。
记者:如您所说,身居海外而以母语写作,这本身是一份寂寞的事业,通常既无法为作者带来在当地的声誉,也很难成为一份职业而带来经济收入。那是什么一直支撑您坚持创作?
答:很简单,喜欢写。在写作过程中,既会经历折磨,也会有非同寻常的快乐。慢慢地,它会成为一个顽固的嗜好。当你找到一个准确的词、写出一个美妙的句子、解开一个情节上的死结,直至完成一篇自己还看得上的小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和快乐值得所有的折磨、寂寞。对于喜欢写作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犒赏。对我来说,母语永远是最贴近心灵、使用起来最自然真诚的写作语言。母语就是随身携带的故乡,只要我仍然在用中文写作,我就没有远离我的童年和故乡。而能够掌握、使用中文这种古老、美丽、深邃的语言,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莫大的幸运。
◆中山日报报业集团新媒体中心
◆文+/记者 冷启迪
◆编辑: 曾嘉慧
◆二审: 张鹏
◆三审: 魏礼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