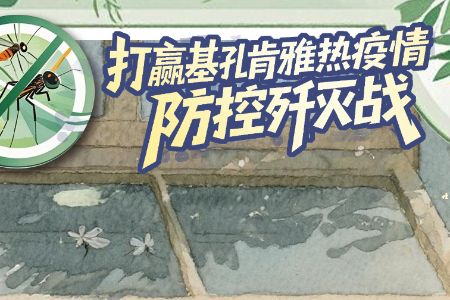从咏马诗说起
古时文人多与驴为偶。杜甫“骑驴三十载”,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早已定格为文学长廊上的一个个经典画面。至于苦吟诗人贾岛骑着一头瘦驴,一路耷拉着脑袋、蹙着眉头又是“推”又是“敲”的,竟与吏部侍郎兼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队撞了个正着,则是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赋驴的诗自是少不了,骑在驴背上的文人们似乎更热衷咏马,特别是咏“马之千里者”。北宋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写过一首《伤骥》:“驽骥同一辀,迟速能几里。当其被问时,举策数耳耳。驰骋心独存,压抑头不起。空传八骏名,未遇穆天子。”让千里马与驽马同驾一车,又焉能分辨出快慢与优劣?往往只能让独存驰骋之心的千里马“压抑头不起”,最终郁郁而终。读罢梅诗,郁怒愤激的千里马的低低嘶鸣犹在耳畔。
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也写过一首《双千里马于甬道试行》:“笑将龙种骋中庭,捷巧何施缓步行。待看流沙遥万里,须臾踏破古丰城。”将“龙种”置于“中庭”,即便如何的“捷巧”,也根本无法一施奋蹄千里;设若回归万里大漠,必定扬蹄如飞,须臾功夫踏破丰城。掩卷之际,局促于一隅、悒郁悲愁的千里马犹在眼前。
最痴迷于咏马者,当属每天骑着小毛驴到处转悠的“鬼才”李贺。据说,李诗中题马诗或句中涉及“马”这一意象的,至少有80多首,约占其存世诗作的三分之一。其中的《马诗二十三首》堪称咏马诗之经典。“此马非凡马,房星是本星。”这样的神骏却“无人织锦襜,谁为铸金鞭?”“只今掊白草,何日暮青山?”如今已“饥卧骨查牙,粗毛刺破花。鬣焦珠色落,发断锯长麻。”李贺笔下,千里马不但没有被当作良马对待,连温饱问题都没法解决,导致形销骨立、毛发残断、憔悴衰惫,教人不忍直视。
文人们缘何都对咏马情有独钟?这可能与“千里马”在文化传统上所承载的意义是分不开的。“伯乐相马”的故事,早已奠定了这一基调。到了《战国策·楚策四》中的《骥遇伯乐》,“千里马”的文化特质又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及至中唐文坛领袖韩昌黎的《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千里马”的文化内涵已完成了最后定型,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当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巨大差距时,文人便开始以笔为鞭,以诗文为马,在纸上纵情驰骋黯然自伤了。马的身上,倾注了不少失意文人的悲愤之情;借马抒怀,自然也成了诸多落魄文人的不二选择。譬如李贺,命途坎坷,为世俗陋见所困,夙志难酬,最后抑郁而终。再三歌吟,实是借马代言,把种种人生况味融于其中。明代的曾益就云:“贺诸马诗,大都感慨不遇以自吟也。”
为什么“古来材大难为用”,既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外部因素,如“独负洛阳才”的贾谊,却被贬为长沙傅;也离不开顶尖人才自视甚高,不善迂回婉转,甚至个性张扬,桀骜不驯,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主观原因,刑场上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的嵇康,就属于此类。
有人说,一部中国文学史,触目多是失意文人的血泪。而“怀才不遇”的文化主旋律的不断重复渲染,更使抑郁愤懑的心态具有了某种普遍性。放眼古今,当文人们自认“腹中贮书一万卷”时,便开始“不肯低头在草莽”,常以“千里马”自许,渴望“有才即见录”,更幻想“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旦“欲渡黄河冰塞川,欲登太行雪满山”,必然一味悲叹自己怀才不遇毫无用武之地。
这于文人而言,或许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所谓的“怀才不遇”,陶渊明和苏轼走的是另一个路子:“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潜,在儒道释中找到了引导自己走出黑暗的明灯,那就是归田、劳作,与自然同乐;苏东坡更多的是借助儒学和佛理,所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话不是苏子说的,但他做得最好,“也无风雨也无晴”,把苟且活成潇洒,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人格的一个典范。
(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徐向东 二审 向才志 三审 岳才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