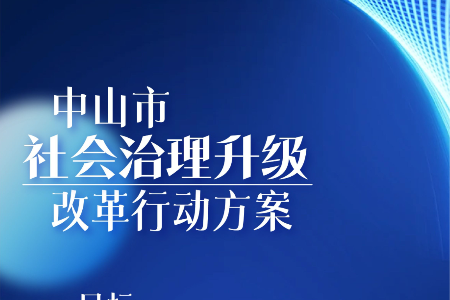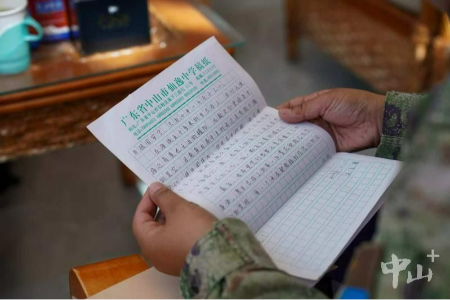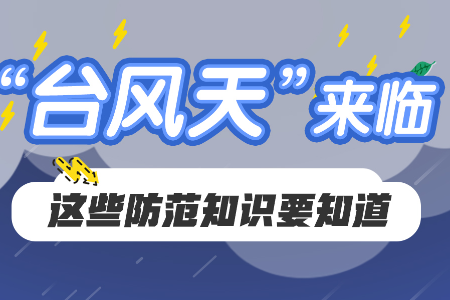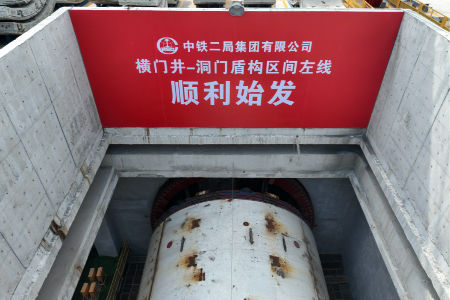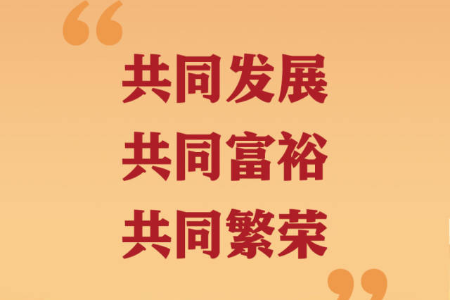梦回《橄榄树》
上周末看了芒果台今年综艺重头戏《声生不息宝岛季》第一期。
看完后有惊喜,也有遗憾。可现在而今眼目下,信息如此发达,观众需求之高,做节目哪能面面俱到、处处完美呢?能够把宝岛季节目做出来,让一曲曲熟悉又陌生的老歌把我们带到那些青葱岁月,也算得上是诚意满满了。
特别感动于经典歌曲《橄榄树》的呈现。
当银发白眉老人胡德夫像往常一样静静地坐在钢琴边,深情地弹唱,太平洋的风显得仍然是那么的和煦温暖。“不要问我从哪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当自由自在的精神穿过山川草原,不知又有多少自由的心灵在此刻逍遥游荡。随着间奏音乐响起,一个巨大的屏幕一分为二,一湾浅浅的海峡分隔开两岸,那英从中间缓步走出,“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世事一场大梦,人间几度秋凉”,真的就结合得这么地巧妙,让《橄榄树》在编曲、演唱、制作诸方面都显得严谨完熟、天衣无缝。
《橄榄树》是三毛应李泰祥之邀写下的作品。原词还有一段:“为了天空的小鸟/为了小毛驴/为了西班牙的姑娘/为了西班牙的大眼睛……”这是三毛旅居西班牙的记忆,也是对她爱人荷西故乡的致意。
当时李泰祥拿到歌词后,觉得不够工整,便改写了一段歌词,加进“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成为我们熟悉的版本。
三毛为此曾经不大开心。她说:“如果流浪只是为了看天空飞翔的小鸟和大草原,那便不必去流浪也罢。”
李泰祥多年后回忆这首歌,则是这么说的:“这首歌就是因为有自由自在的精神才被大家认同。为了表达出这种自由自在的理想,所以才改写成后来的歌词……我自己经常被传统束缚,生活上有许多框架,总觉得处处碍手碍脚,一心希望能自由自在地写作创作。《橄榄树》所体现的,就是我对个人生命完整的自由与追求完善的理想之寄托,可以打开胸襟,不再拘泥某些传统……这些都是我真正有感而发的。”
据说,当年《橄榄树》无法在电视、电台公开播放,是因为台湾方面害怕“我的故乡在远方”会挑起敏感神经;又一说是忌惮“流浪远方、流浪”会鼓励青少年离家出走 ……然而,这些毕竟未能阻止《橄榄树》的广为传唱。
马丁﹒路德﹒金说得好,“黑暗无法驱走黑暗,只有光芒可以;仇恨无法驱走仇恨,只有爱才可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正确”,还有人民大众在悲欢离合中对时代的感觉,那就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梦田,都有自己“梦中的橄榄树”。
话说《橄榄树》与我还蛮有缘分的,我也从来没想到过这首歌还曾经是我当兵入伍的敲门砖。
记得征兵体检过关后,接兵干部到家走访。当时他问我有何专长,我说我会唱歌,那我就唱首歌吧。当时我就唱了《橄榄树》。可能在唱的时候某一句歌词或是某段旋律真正触动了接兵干部的神经引起了他的共鸣吧,我便光荣入伍了。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我想和我当时的心境非常有关系,高考失利,对前途迷茫,真想逃离熟悉的世界,去外面闯荡,这可能就是我理解的“流浪,流浪远方……”吧。
这些年来,有多少像我一样为了生活在外打拼的人们,他们或人在旅途,或浪迹天涯,或春风得意,或悲伤怅惘……大家都在快节奏的生活,但在逐梦追梦的过程当中,突然在某个瞬间或某个节点里,都有被这首歌缥缈的音符击中灵魂深处的经历,从而引发起心灵对乡愁的强烈共振。那是因为随着岁月变迁,时空把故乡的概念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故乡真的就在远方,家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家了。
无可否认,都市浮华的诱惑与乡土情怀的纠结、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痛苦抉择是我们对工业社会的本能反应,但正如罗大佑《鹿港小镇》里写的,“在梦里再度回到鹿港小镇/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是的,精神的家园永远都在远方,也在前方,追梦的人脚步永远不会停止。几回回梦里回“鹿港”,少年应该还是从前的少年,鲜衣怒马,愁滋味不识;初心不忘,没有一点点改变,这应该就是梦回《橄榄树》的魅力和神奇之所在吧。
(不收微信来稿。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徐向东 二审 向才志 三审 岳才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