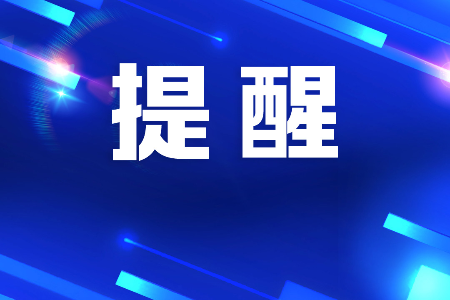凤凰山的栀粽
那年端午节快到了,表舅说要送粽子来。在每年端午节,表舅总会如期给我家送来凤凰栀粽。这一送就是五十多个年头了。
家在凤凰山区的表舅,原是我家一个潮州俗称“粉葛藤亲”的远房亲戚。1962年,因为高考落选,他同几位凤凰镇的同学到潮州复读,借住在我家。不过,表舅他们高考又一次落榜,回到凤凰务农。过几年,表舅成了家,逢年过节随民俗做粿做粽子。从娶亲这年起,在端午节来临前夕,表舅挑着一对采茶小筐,到潮州城里走亲戚送栀粽。
表舅的栀粽从选料到制作都十分讲究。栀粽呈长方形状,犹如精巧小枕头,剥开包裹的绿叶子,呈现宝石般金黄晶莹,一粒粒糯米像珍珠,香气扑面而来。一入口,绵软、黏韧、甘爽,让人含嘴里不忍咽下。胃口好的,吃冷藏的栀粽更有另一种弹牙、劲道、清凉的感觉。凤凰栀粽不但营养丰富味道好,还是消暑开胃的美食,是潮州历史悠久、远近闻名的特色小吃。
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苞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粽属于“籺”的一种,籺是人们在逢年过节时用来祭祖的贡品,逢年过节做籺拜祭祖是古老的传统习俗。籺有很多品种,不同的节日会做不同的籺。粽籺是端午节祭祖贡品。东汉末年,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煮熟,即为广东碱水粽。凤凰栀粽也是广东碱水粽其一。
听表舅说,凤凰山里人做的栀粽,要用野树野草烧草木灰,并且尽量寻找“埔姜”和“甘亩”的枝叶,烧出草木灰泡的栀水就特别香。粽叶粽绳也有讲究,用山上野生的箬叶,粽子煮熟后香味更浓郁,绑粽子用的是从山上割来的芦草。做粽子的米是自家种植的糯米,一颗颗“白莹如玉”。一个小小的粽子,几口就能把它吃完,可制作起来却费工费神。端午节前几天做准备,粽叶洗干净用水泡着,烧开水冲洗草木灰过滤出栀水来,将糯米淘洗干净后在栀水中浸上一天一夜。隔天,从栀水中把糯米取出沥干水分就可以包粽子。然后,将大鼎里的水烧开,放入包好的粽子用柴火煮上十几个钟头,才算大功告成。
也因此,我不时会想到为了做这粽子,表舅在凤凰山遍野荆棘中,寻找“埔姜”和“甘亩”枝叶的艰辛;在陡峭的高山,收割箬叶的危险;在崎岖山路前,负重爬坡的苦累;夜里昏暗油灯下,女人、小孩一起挑出混在糯米中粳米的麻烦;烟雾缭绕的灶间,烧火煮粽子十几个钟头的“煎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凤凰山区到潮州公路是泥土路,山路七弯八拐,坡陡峭,路不平。表舅到城里送粽子,要天蒙蒙亮出门,走几里路到汽车站乘车,一路颠簸两个多小时才到潮州。城里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去几个亲朋好友家要靠脚板走上两三个钟头。下午,即便赶得上车,回到凤凰家里也是天漆黑了。来一趟城里不容易,表舅就是这样年复一年送粽子。
那时,物资紧缺,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居民凭证供应口粮,而农村农民要按任务交公余粮,粮食也不充裕。过来人都知道好些年份,农村“春尾”时缺粮的窘状,而山区情况更甚。那时城里人没有做栀粽,市面上也没得卖,表舅送的栀粽在城里可是稀罕之物。那个年代,表舅把不多的糯米省下来做粽子送亲戚,平时得多节俭。后来,经济状况好了,表舅送的粽子就越来越多了。他还惦念着我在外地工作的小妹也喜欢食凤凰栀粽,让我记着寄给她。
栀粽,让我家和表舅家尝到了亲情味道,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显得越来越浓。年纪大了,念叨的事情也多了,表舅会隔三岔五打电话嘘寒问暖,问问我母亲身体好不好,请我们到凤凰去走走。其实,我们也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亲舅舅了。
表舅给的不是简单的粽子,它传递的是五十年的情啊。
(不收微信来稿。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 徐向东 二审 向才志 三审 岳才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