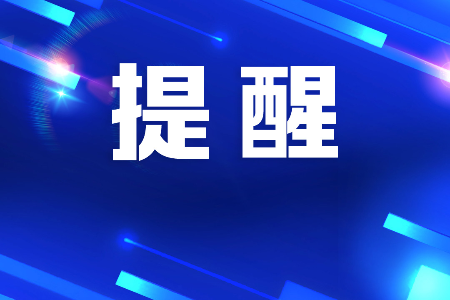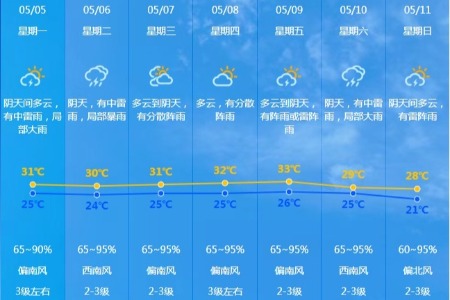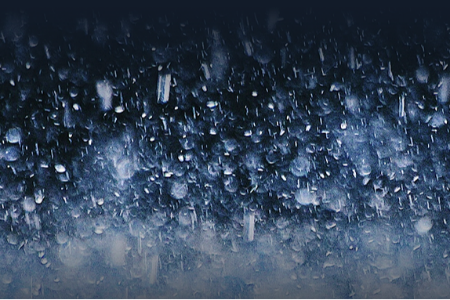母亲的南瓜饼
一想到故乡的蔬菜,就想到母亲煨的南瓜饼,那个香呀。
南瓜贱生易长,瓜、花、叶、藤蔓,都可以做食,藤蔓被冠以一个高贵而响亮的名字:龙须菜。南瓜在农村还当杂粮,更可喂牛、喂猪,乡下有个说法,一担南瓜抵半箩谷,因而家家户户种植,以补充粮食。屋前屋后,山边河边,地头地尾,能让瓜藤洋洋洒洒攀爬的地方,都能看到南瓜藤蓬蓬勃勃生长的倩影。冬天,收获南瓜,家家的厅堂,都堆放着一大堆圆滚滚、硬邦邦的南瓜,顽皮的小孩当凳子坐,当圆球滚动。
我家门口几十米外有一口池塘,宽四五米,长二十多米,水深一米左右,时浊时清,偶尔有鸭、鹅戏水,生产队投放过鱼苗,雨季跑光,一无所获,便废弃了。母亲快人一步,在塘堤边挖了一个两平方米大小的瓜罕,认为人有房住,遮风避雨,才安全,南瓜藤也要有个棚爬,才能防止畜生的践蹋。冬天驾临,粮食归仓,田野空荡,雨水减少,河瘦渠枯,池塘露出黑黝黝的塘泥,乡村进入乐悠悠的农闲季节。
母亲带领儿女,抬来竹、木,挥刀拉锯,木段插入地下作柱子,粗硬的石竹作主梁,瘦小的凤尾竹作次梁,竹篾作绞绳,搭了一个前低后高的瓜棚,有二十多平方米。又用竹片作篱笆,严严实实围住瓜罕,起一堆塘泥作肥料。首年获得了大丰收,摘了十多只南瓜,每只有二三十斤重,瓜罕成为家里新开辟的一口“米缸”。
盛夏,雷,轰轰炸响,雨,洋洋洒洒,南瓜花鲜艳(一种带果,一种无果,无果的可以摘食),叶儿碧绿,蔓儿脆嫩。母亲待雨过天晴,摘满满一箩筐回家,清洗干净,用手拧断,放进锅里煮,只放点油、盐,有时打一两只鸡蛋,清甜、爽口、开胃,清凉解暑。我们一人盛一碗,当汤当菜又当饭,如食人间美味佳肴,狼吞虎咽。
米饭不够,南瓜来凑。冬天,寒夜漫漫,天寒地冻,母亲为使我们少起床拉尿,晚晚煮饭,但饭很少,炒满满一瓦盆南瓜,碗底装一点饭,上面全是南瓜。我们养成了习惯,扒到米饭的时候,又装南瓜,又粉又甜,相当可口,食得开胃,添两三次,肚子就饱了。
我最喜欢母亲做的煨南瓜饼,做法简单,切一块瓤红肉甜的南瓜,刮去皮,放进锅里清水煮,熟透后捞起来,搁在案板上放凉。抓一把糯米粉,或面粉、木薯粉,增加黏性,与南瓜肉一起搓成粉团,随意添加点调味料,如盐、糖、蜂蜜、葱粒、韭菜粒、芝麻、生菜丝、花生碎、黄豆碎,薄荷叶、紫苏叶、桂花、杜鹃花,身边有什么,四时有什么,就添点什么,不需要刻意准备,什么也没有,也没关系,南瓜糖分足,甜味浓。尔后将粉团压成一块块薄饼,放进柴火熊熊的灶膛里煨,偶尔翻动一下,均匀受热。十分钟左右,南瓜饼熟透了,从灶膛里翻出来,表面浮起一层焦巴,有一股烟火之香,植物之香,又韧又甜,很有嚼劲。
我们兄弟姐妹,每天早上起床,一人拿一块刚刚翻出灶膛的煨南瓜饼,乐悠悠走出家门,一小块一小块撕下来放进嘴里,边嚼边往学校走,一路飘香。总听到母亲远远在背后提醒:小心点,别烫伤手。
那年,不知谁家的牛,拱破篱笆,连瓜藤的头也扯起来食掉了。三姐对南瓜最上心,辛勤浇水除草施肥。三姐与南瓜,有了深深的感情,伤心得眼角流泪。那天晚上,母亲做好饭菜端上桌面,三姐依然气鼓鼓,不动碗筷,说食不下,嘴巴嘟嘟哝哝骂了一句话,扬言要找生产队干部反映情况讨个说法,查出是谁家的牛食了瓜藤,要赔偿,不能白白吃掉。我想到冬天上学没有煨南瓜饼吃,会挨饿,因而发声支持三姐。
母亲从不与人争吵,自有好人缘,头疼发热,伤风感冒,有七姑六婆来问候,村民办什么红白喜事,爱请母亲去帮忙。母亲很珍惜这种融洽的人际氛围,此时,心头隐隐作痛,眼角发湿,依然没有发火,没有骂人。
母亲将一块鸡蛋煎萝卜干挟到三姐的饭碗里,开导说:女儿,消消气,就当没种过这垅南瓜。邻里之间,要和和气气。瓜没了,可以再种,人伤了心,撕破了脸皮,一辈子愈合不了。我们种瓜,为了得到好收成,不是为了伤心伤情。
三姐点点头,抹干眼泪,拿起了筷子,默默扒饭。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饱食一顿炒南瓜、龙须菜、南瓜饼,品的是一种乡愁,一种教诲,一种对母亲的深深怀念。
(不收微信来稿!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①文体②真实姓名③银行户名④银行账户全称细到支行⑤账号⑥身份证号码⑦联系电话⑧联系地址。文责自负。)
◆中山日报社媒介拓展中心
◆编辑:徐向东
◆二审:韦多加
◆三审:黄廉捷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