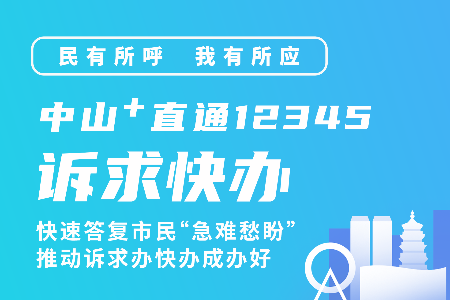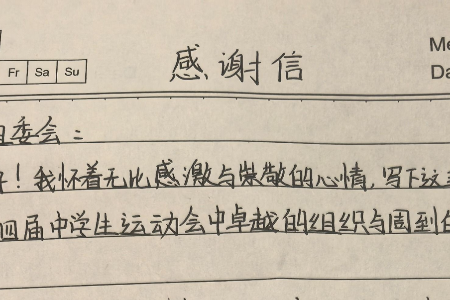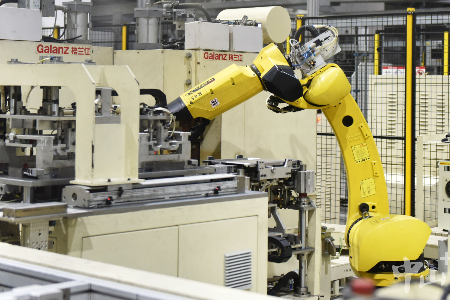我的乒乓梦想
少年时期,我是疯狂地热爱着乒乓球的。

那个时候,想打个乒乓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周围的同学都是“三无”,第一没有乒乓球、第二没有球台、第三是没有球拍。
球台,学校是有的,就放在学校的一个房间里,可惜门锁得死死的。我和伙伴们曾无数次扒着窗户看着流口水,墨绿厚实的台子,边上刷着白色的边线,中间撑着墨绿色的网子。听说要校长同意才能开,还有人说谁谁谁有钥匙也能开。然而打听归打听,其实最终谁也没有壮起胆子找一下校长,或者找那个戴钥匙的人。后来学校起了一场火,好像把台子也烧了,我们也从来没有在里面打过一次球。
乒乓球也是个稀罕东西。伙伴们只有要一个乒乓球,那肯定后面跟了长长一串。“象”牌1毛钱一个,“连环”要2毛4一个,那个时候口袋里哪有1毛钱啊,即使有,马场的门市部也没的卖,要到尼勒克县城的商场或者哪里的物资交流会去买。而这对我们,似乎又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球拍就更不用说了,每年过年,爸爸会带我到县城的奶奶家拜年。奶奶家的对面,就是尼勒克商场,上面就摆着一副火红的球拍,4块钱一副。虽然兜里没有一毛钱,还厚着脸皮让营业员阿姨拿下来过好几次,那火红的颗粒胶皮,黄色的球板,“红双喜”的标志正正地印在球柄上,爱不释手地反复看来看去,最后还是不舍得地还了回去。
然而,上面这一切都不能阻挡我对乒乓球的热情。
没有台,下课以后就把课桌拼起来,找两块砖摆在两边,然后找个树枝中间一拦,便成了我们的乒乓乐园。没有球,爸爸刚好买了几盒回来,放在鸡窝里,每个位置放几个,说这样能让母鸡多生鸡蛋,于是我又拿一个出来,坏了就换回去。没有球拍那就拿碎玻璃、用木板锯一个形状出来,甚至直接用本书,就这样凑合,也能打成一场欢乐的乒乓球,一直打到太阳下山还舍不得回家吃饭。
后来,条件慢慢好了,父亲给了我8块钱,让我买了一对“红双喜”球拍,到了手就找来胶布,周围牢牢地粘好。学校的后面,也空出一块地来,做了几张水泥台夏天打球就是天堂,下了课,让红玲把书包帮我背回去,拿着球拍就到球场打。人太多,一个个排队“做皇帝”,赢了留着,输了下台,直到高年级同学晚自习前一刻,灯光亮了才跑回家吃饭。到了冬天,尤其是寒假,就得先把台子上和场地周围的雪扫干净,然后戴着面帽穿着大棉袄打,不一会头上就冒出热腾腾的蒸汽来,头发上、眼睫毛都结着白霜,手胀红胀红的,不打高兴绝不罢休。
最让人高兴的是,学校还居然成立了乒乓球队,教练是体育老师外号叫“胡老大”的,乒乓球很厉害,每次马场比赛,他都是一号种子,大家都淘汰下去了,再和他打,就这样他还年年都是冠军。他让我们围着乒乓球台一边转圈一边挥拍,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有一次,马场组织乒乓球比赛,我居然拿了少年组冠军,奖品是一本影集。我曾一度脑子里只有乒乓球,甚至想当职业运动员,父亲知道了倒没说什么,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要是想出成绩,你这个年龄要在省队才有机会”。
再后来,回了广东,大学和参加工作就慢慢打得少了,加上我又是兴趣很广泛的人,啥都爱玩,可惜啥都玩不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摄影、文学。除了读书不辍以外,其他都是心血来潮来几下,过了也就放下了。再后来,工作越来越忙了,也更少打球了,其实也不是没时间,就是慢慢懒了,不太想动弹了。
其实现在想,当初的梦想不过是一张木球台、一个乒乓球、一个球拍而已。
(请勿微信投稿。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一投一稿,并注明文体。文责自负。
◆中山日报社媒介拓展中心
◆图/资料图片
◆编辑:徐向东
◆二审:向才志
◆三审:魏礼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