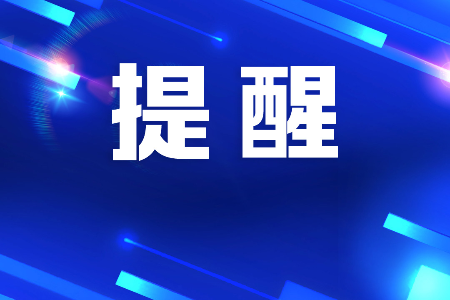苇中听蝉
我对母校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校园绿树中的蝉鸣,那短促、激越、高亢的鸣唱,让人有种安然若素的心境,和着课堂那朗朗诵读,教室里充满了诗和远方的浓烈氛围。

如果用“半亩方塘一鉴开”来形容苇荡中学,我认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两排四间教室宿舍加几间食堂,有五个半亩大的方塘犹如映月的镜子镶嵌其间,四角成方地静卧在教舍门前,塘边四周栽种一色水的柳树。开学后,到了当春乃发生时,这些柳树返青早,发芽快,给校园早早增添了盎然春色,陪伴学习的我们一起成长。
家乡草木丰茂,房前屋后的树上,从初夏到初秋,蝉鸣歌声没有间断过,大人说“听到知了叫了,真正的夏天才到来”。所以,我始终记住蝉鸣了才是夏天。小时候也跟着年龄大点的伙伴去树丛寻找蝉蜕,一分钱两只卖给中药站,将有筋道的面团粘在竹竿顶端用来粘捕蝉,有时粘住又被挣脱,有时没粘到却被蝉洒了一脸的蝉尿。蝉鸣在家乡习以为常,只身一人乍住学校时,再听到耳朵早已听出老茧的蝉鸣,竟然有了一种亲切之感。一次我坐在东头大柳树下看书,树上蝉鸣声声,书中字字珠玑,入神如无人之境,班主任魏标老师悄悄地走近身后浑然不知,当魏老师故意走到面前时,我才慌慌张张地站起,脸红嗫嚅,戴着黄边眼镜的魏老师笑而不语,点点头,摆摆手,姗姗而去。偶遇一只蝉误飞教室后窗台,我会想难不成它也来偷听讲课,抑或是想与我们比赛朗诵?默默对视,能让我发呆好长时间。
重返校园是毕业后好几年的事,带着临海镇政府办的介绍信,去档案室查找我的学生档案,在校门口李同中校长一眼便认出我来,查找档案顺风顺水。李校长和我四叔曾在一个学大寨工作队共过事。我伫立在塘边的大柳树下,阳光透过密密层层的柳叶枝条,在岸边洒下斑驳的光影,水中倒影清晰如昨。校园随便哪棵树上都有蝉鸣,凭我从小对蝉的熟悉,仅听声音就能判断它的方位和高低来,但碰到几只蝉在一棵树上鸣唱,真像宋朝诗人杨万里描写的那样,“听来咫尺无寻处,寻到旁边却不声”。
蝉的声音听惯了声声入耳,仿佛它来自每一片绿叶,不知疲倦的鸣唱在心里便漾起层层绿意,许多时候我把蝉鸣当作老师的讲课声,脑海中闪过从一年级到高中再到南师大诸位老师的身影,叶老师、解老师、于老师、胡老师、王老师、谈老师等等,他们不同年级任教传授犹如四季的接力。人与自然同理,在这个蓬勃生长的季节,无论你承不承认,你都无法拒绝成长。我在政府上班的路上,但凡撞见启蒙叶庆宝老师时,我都主动下车打声招呼,叶老师是南京客籍,青呢子黑皮鞋,七十年代十分显眼。我毕业后见到高中班主任时,魏老师已经退休在家赋闲,当我和同学们再去魏老师家时,只见到带着永恒不变微笑的黑框照片。点滴师生情,仿佛如昨天。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王昌龄在多事之秋,把蝉鸣写得空灵,而我的家乡时令已入八月,天气依旧炎烈,初秋里的蝉鸣,自然也就成了告别的绝唱,少了合唱气势,但还一样洪亮,毕竟沉寂泥土下,在黑暗中蓄力,默默成长,漫长等待才蜕变成蝉,珍惜来之不易的阳光明媚与绿树花香,迸发出激情振翅唱响生命的时光轮回。蝉儿不知心里事,岁岁蝉鸣有尽时。毕业离开校园前的晚上,月光皎洁,挥泪话别,那天蝉鸣了很久很久……
蝉鸣无痕,翻遍夏秋所有的绿叶也找不到一丝一缕印迹,它的歌声唱给夏,唱给绿叶,唱给光阴,唱给喜欢的人;岁月有印,容颜渐老,鬓发染霜,今非昔比,蝉鸣依旧。校园外遍植垂柳,到处蝉鸣,心有乡愁,此声胜有声,只是有时人们忽略了它们不倦的嘶鸣。打开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唐诗风骚,宋词遗韵,虽未熏陶点化,倒也听得见悠悠蝉鸣。我和同村同学把行李合在一起还像报到时用小扁担轮流挑着回家。温润的校园,有过激情,梦想,感动;也有过彷徨,苦恼,无奈。一路绿树一路蝉鸣,走进广阔天地。
“落日无情最有情,遍催万树暮蝉鸣。”应该感谢蝉,每当听到蝉鸣,我自然就会想起青涩的求学岁月,诲人不倦的最亲爱的老师们。
(这是一个共享、互动平台。“文棚”面向全球华人开放,供作者和读者交流、推送。其“写手”栏目向全国征集好稿,凡当月阅读量达6000次,编辑部打赏50元/篇,12000次则打赏100元/篇;另外,每月由文棚主编推荐5篇优秀作品,给予50-100元奖励。优秀作品可以参加季赛和年度总决赛。请一投一稿,并注明文体。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全称、户名、账号等。文责自负,发现造假、抄袭、套改等即予曝光。)
◆中山日报社媒介拓展中心
◆图+1/徐向东
◆编辑:徐向东
◆二审:韦多加
◆三审:魏礼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