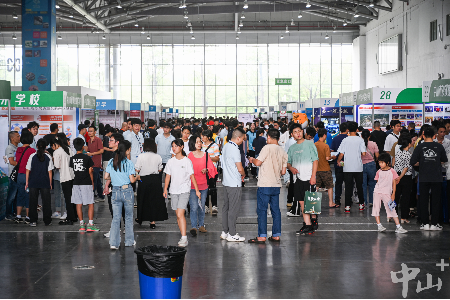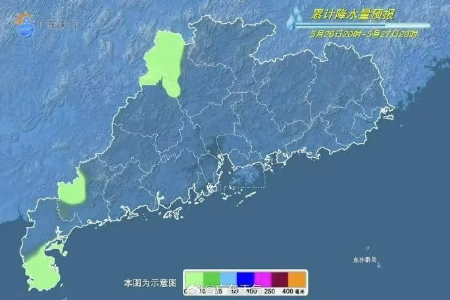沙漠里的皂角树
去撒哈拉之前,我在脑海里无数次幻想过沙漠里的奇景。在此驻足的数十天,梦中的景观终于一一变成了现实。
我的眼前真的出现了半壁汪洋,半壁黄沙的奇观;我看见火红的夕阳在沙漠的尽头燃烧、炸裂、飘摇、坠落;我躺在滚烫的沙窝里,倾听耳边呜呜的沙鸣,遥望明朗的星空,人生第一次清晰地凝视着牵牛织女星隔着浩瀚的星河无语凝噎;我把自己扔进四驱越野车里,任身体随着起伏不定的沙丘翻越奔腾;我坐在三毛笔下的贝都因人身边,沦陷在他们茫然的眼神和手中翻飞的薄饼里;我近距离地观察古埃及王者们的雕像,同他们分享跨越世纪的沉默;我靠在斑驳的方尖碑下,我潜入红海浩渺的碧波中,我游走在北非热辣的风沙里……是的,撒哈拉几乎满足了我对沙漠所有的幻想与激情。甚至数年后,回想起那一幕幕的场景我依然激动难忍,泪湿眼眶。但我不曾想到的是,吹过那么多黄沙,见过那么多风光,听过那么多故事,深深烙印在我脑海最深处最让我震撼的却是那株皂角树。
一株黑褐色的皂角树孤独地挺立在一望无际的黄沙里。不晓得它已经生长了多少年,只见得矮矮的树冠黑中透着褐色,树上光秃秃一片叶子也没有,枝丫上却缀满了黑褐色如生锈了的小镰刀一样的皂角,在北非的风沙中僵硬地舞动着。
那一刻,除了惊讶,我更多的是感动,甚至流泪的冲动……因为在那一刻,家乡村头那棵皂角树毫无征兆地冲进我的脑海,与眼前这颗皂角树合二为一。那一刻,我分明是站在北非的沙漠里,却深深感受到来自地球另一端家乡的召唤,感觉自己回到了遥远的家乡,站在村口的皂角树下。那一刻,我的认知混沌起来。北非和东亚的隔着的岂止是万水千山,撒哈拉和大西北关中平原隔着的岂止是千山万水,但这两个原本遥不可及的地方,却因为一棵皂角树,在遥远的地球两端神奇地相遇了。两棵皂角树不期而遇的那一刻,早已褪色的记忆,早已尘封的家乡和亲人却渐渐清晰起来。
老家的村口有棵皂角树,好像从我记事时就有了。对这棵树的成长过程我早已经没了印象,只记得树很高、很瘦、很干、很硬,树上缀满了嫩绿色的皂角。皂角在关中平原清冽的秋风里疯长,几乎几天时间就长到尺把长,颜色也从浅绿变成嫩绿、翠绿、老绿、浅灰、浅褐、深褐,直至最后变成一个个黑褐色粗硬的小镰刀。
爷爷找来长长的竹竿,在竹竿顶绑上一节铁丝弯成的钩子,我们西府人管这叫钩搭。这时候,我们姐弟几个已经像等不及的小燕子,围住爷爷催着去钩皂角。于是夕阳西下的村头,就看见我们姐弟簇拥着扛着长长钩搭的爷爷,神气活现地朝皂角树走。爷爷站在树下钩,钩掉的皂角落得满地都是,我们姐弟绕着树跑来跑去捡,不大一会儿就捡了满满一筐。一看框满,爷爷也不顾我们姐弟还在树下上蹿下跳,一把拎起筐挎在胳膊上大步就朝家里走。看到爷爷走了,我总是第一个跑上去拽住他的衣襟跟着。走到家门口,奶奶照例坐在门墩上晒太阳。爷爷把筐子腾一下甩在奶奶面前,边擦汗边说,老婆子,给你,够你用一年的了。正眯眼打盹的奶奶被吓了一大跳,回过神看到面前一大筐皂角,眯缝着的眼立马亮光闪闪。奶奶抬头看看满头大汗的爷爷,照例唠叨。你个老头子,一头汗一头灰,脏死了,也不知道去洗脸换衫……爷爷毫不理会奶奶的唠叨,举起袖子抹抹额头的汗珠,捞过奶奶身边的茶壶,咕嘟嘟喝一气。然后一把拽起满筐的皂角来到院子里,舀来一大盆水,把皂角一股脑倒进去,拿着刷子一个个洗刷起来。我也凑热闹,双手在皂角盆里抓。湿了水的皂角滑溜溜的,小鱼儿一样总也抓不住,不一会儿,我和爷爷就浑身都是水。
奶奶踮着小脚跑过来,一看我们爷儿俩这阵势,边推爷爷边呵斥说,谁要你洗,你看你个脏样子,把娃的衣服也弄湿了。去去去……爷爷笑呵呵地走开蹲在旁边,我也跑过去搬来小板凳放在奶奶身下,奶奶坐下来开始一根一根慢慢洗皂角。洗过的皂角湿淋淋的,被爷爷奶奶铺平在旁边的大筛子里,颜色愈发显得黑亮清透,隐隐泛着红光。秋日傍晚的阳光还很毒,半天功夫皂角就干透了。奶奶把大半的皂角收起来装在袋子里,留下几颗拿到院子里的大石头上,用棒槌使劲捶起来,一个个皂角在棒槌底下开裂,溢汁、冒泡……一会儿,大石头上就满是皂角沫沫和泡泡,泡泡不断地聚集、爆裂,清苦的香味在石头上流淌,奶奶的手上、身上,整个人都散发出皂角的香味。
奶奶把砸碎的皂角沫收集在一个大罐头瓶里,拧紧了收起来。从此,我就看见奶奶洗头发的时候打开罐头瓶,挖出一点皂角沫抹在雪白的长发上轻轻地揉,一会儿头顶便堆满了雪白的泡沫,奶奶的白发和皂角的白泡泡堆在一起像白云一样,小小的我都分不清楚了,总喜欢上去抓。奶奶洗过的头发的香香的、顺顺滑滑的搭在瘦小的背上,格外的好闻。洗衣服的时候,奶奶又把皂角沫拿出来,抹在衣服上揉搓,于是暗沉的衣服被奶奶洗的清清亮亮地挂在院子里,整个小院都飘荡着皂角的清香。村里的大人小孩都被吸引过来了,大妈婶子都问奶奶讨要皂角,奶奶笑着拿出存放皂角的袋子,每人三根五根地派发。这时候爷爷走过来一把拽过袋子,急吼吼地说,这是给我家老婆子用的,你们谁要我明天去钩,你们去树底下拿。大妈婶子都笑呵呵地瞅着我奶奶,奶奶一下子脸红了,骂道,这死老头子,越活越小气了。我们小孩可不管这些,就在奶奶晾晒的衣服中间跑来跑去捉迷藏,回荡的笑声把皂角的香气都赶跑了。
二十几年过去了,我早已离开关中平原上那个皂角飘香的小村庄。我一直是个不太恋家的人,我更希望去更多陌生的地方放逐自己,于是我努力走出小村庄,走出爷爷奶奶的视线,走向远方。我在遥远的他乡如鱼得水,我甚至走进书本里描绘的更遥远更陌生的远方追逐自己的梦想,可是我完全没想到,在梦想中的撒哈拉看到皂角树的那刻,我又回到尘封的家乡,来到村头那颗皂角树下,看到钩皂角的爷爷、见到用皂角洗头发洗衣服的奶奶,我闻到了奶奶身上香香的皂角味儿…….
站在撒哈拉呛人的风沙中,我的泪珠大颗大颗地滚落……
(这是一个共享、互动平台!“文棚”面向全球华人开放,供作者和读者交流、推送。其“写手”栏目向全国征集好稿,凡当月阅读量达6000次,编辑部打赏50元/篇,12000次则打赏100元/篇;另外,每月由文棚主编推荐5篇优秀作品,给予50-100元奖励。优秀作品可以参加季赛和年度总决赛。请一投一稿,并注明文体。投稿邮箱:2469239598@qq.com,1600字以内;请注明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全称、户名、账号等。文责自负,发现造假、抄袭、套改等即予曝光。)
◆中山日报社媒介拓展中心
◆编辑:徐向东 实习生 袁隽清
◆二审:韦多加
◆三审:魏礼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