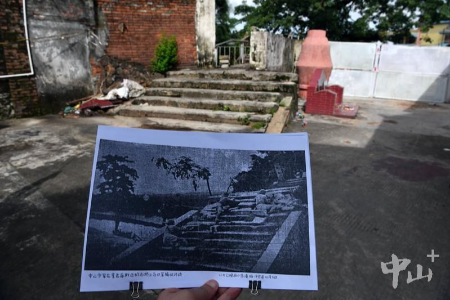灯笼挂起来,春联写起来,浓浓的中国年味就出来了。徜徉中山街头,举目皆是中国红,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爷爷写的春联。
爷爷写春联已经是很遥远的事儿了,但那情那景已然镌刻于心,清晰如昨。我记忆中的年味,是从那年那月爷爷笔下的那一缕缕墨香开始的。
腊八过后,依山傍水的美丽小村庄——高车头村就开始为过年热闹忙碌起来了。勤劳的女人们为制作一种叫“叶粑”的过年必备美食做各种准备。这是一场全村“叶粑”技艺大比拼,谁家的叶粑做得好和谁家的女人最心灵手巧聪明能干成正比,腊月里叶粑的特有清香缭绕整个村庄。而我的爷爷则在忙活他的拿手好戏---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写春联。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春节习俗不尽相同,但千家万户贴春联的习俗却是一样且必不可少的。它是中华民族上千年来流传下来象征喜庆吉祥、表达人们美好祝愿和迎春纳福的优秀传统,也是一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全民参与的最瑰奇最盛大的文艺活动。
爷爷读过几年私塾,深谙国学,写得一手令人叫绝的书法,爷爷未出车祸前,洪家所有的春联都是他亲笔写的。
那时的我除了掰指头盼过年有好吃有喝的,就是盼爷爷写春联。
腊月二十前后,爷爷写春联的良辰吉日到了,这是爷爷一年中最具仪式感的大事,也是他一年中的高光时刻,亦是我最快活的日子。他要写完我家和叔叔家共三间大屋的所有春联,得花上大半天功夫,这一天我都黏着爷爷,做他殷勤的跟屁虫,写春联时的得力助手。
吃过早饭后,爷爷郑重其事地把平时吃饭用的八仙桌摆在厅堂中间,细心地擦干净后取出一摞大红纸铺在上面,我则把剪刀、尺子、墨汁等准备停当。爷爷拿起剪刀轻车熟路地“咔擦”几下把红纸按大门、小门、侧门大小裁剪成不同尺寸,摊开,铺平,这时我知道爷爷就要拉开架势进行大动作大手笔了。
我赶紧把墨汁倒在事先准备好的大粗瓷碗里,只见爷爷执笔蘸墨,目光如炬,物我两忘,笔走龙蛇,跌宕有致,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笔势雄健洒脱,线条粗细藏露皆变幻无穷,笔划断连辗转朴实无华,兼纳乾坤。横批“鸿禧”两个大字尤为神妙无比。我站在八仙桌另一头负责拉纸角,紧张地屏息凝视,不敢言语,生怕会打扰爷爷写错字。事实上也不得言语,奶奶早警告过我今天不得乱说话,虽说童言无忌,奶奶还是担心我口无遮拦说一些不吉利的话。此时有村里的叔伯经过会进来围观,有文化没文化的都会为爷爷的字啧啧称赞。见有人围观,我特别兴奋自豪,更起劲为爷爷红袖添“墨”。我想象中的红袖添“墨”,赌书泼茶,快意人生,不是与一位翩翩公子,而是为爷爷。
爷爷每写好一副春联,就让我铺到西屋地上风干。我如领圣旨,小心翼翼地捧着氤氲着墨香的春联铺在地上,用小石头压住四角,让其风干。一天下来,铺满一屋大大小小的春联,俨然一小型书法展,甚是壮观。
爷爷写的大门春联年年都是“椿萱并茂,兰桂藤芳”从未变过,跟别人家的“福星高照,泰运长行”、“花开富贵,竹报平安”这些容易理解的春联明显不同,年幼的我不懂,问其原因,爷爷笑而不答。后来我才知道,语出明代程登吉的《幼学琼林.祖孙父子》:“父母俱存,谓之椿萱并茂;子孙发达,谓之兰桂腾芳。”这样一比,我们家的春联比普通的春联就有内涵、有底蕴、有格调、有文化得多了。更妙的是爷爷把他名字“德椿”的“椿”和奶奶名字“敬芳”的“芳”嵌入其中,堪称“村中第一联”,成为一道独特风景,也是我们家过年最别具一格的年味。
到了除夕那天,我们兄妹从西屋拿出爷爷写好的春联,用母亲熬好的浆糊,欢天喜地给父亲帮忙贴上。猪牛鸡鸭圈还要贴上“六畜兴旺”,灶王爷那还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的小条幅。
春联一贴,整个家顿时红彤彤的眼前一亮,喜庆吉祥气氛一下子全有了,正如王安石《元日》里的图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期盼日子越过越红火,希冀生活越来越亮堂的美好愿望和祝福全在爷爷的春联里。
春联贴完,母亲做的年夜饭也上桌了,一家人围坐热热闹闹地吃着团圆饭,村中的鞭炮声也陆陆续续地响起……
也许就在那时我心中埋下了热爱传统文化的种子,原来文字还可以这样写,春联可以这么美。也许这就是家学渊源耳濡目染,也许这就家风家训潜移默化,我家和叔叔家兄弟姐妹六人都传承了“诗书继世,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靠读书改变命运,走出了小村庄,走向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爷爷后来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手术最终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大难不死的爷爷变得脑袋不太灵光,手脚不太灵便,自然也就不能写春联了。打那后,我家和叔叔家春节只能买印刷体的春联,这当中的年味就少了很多。
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十四年,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农民离去自然不会在这个世界掀起什么波澜,但爷爷和他的春联却永生在我们心中,成为一座家族丰碑。
三阳始布,四序初开。转眼又是春风十里,爷爷生前惦记着年久失修不能住人的老屋已推倒重建为一栋三层小楼在春节前入伙。父亲坚持不把老屋建成“别墅”式而是按它原来的“品”字型结构格局重建,我想这也是一种怀念与传承,新屋落成,也让离乡别井多年的我们有了安放乡愁的去处。那个曾经拼命要逃离的高车头村如今成了人到中年的我们最想回归和治愈的故园,出走,归去,人总要回到自己的起点,也是终点。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年终岁末还乡是每个漂泊在外游子的春节信仰和精神图腾。辛丑牛年春节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霾下,响应国家号召,我选择了留在中山“就地过年”。这个回不了家的春节,通过一根网线,用“云过年”的方式与亲人“云团圆”以慰乡愁,让那缕缕墨香与时俱进地融入高科技元素,我想,爷爷在天之灵也是理解和欣慰的。
工作单位:中山市东区柏苑中心小学
◆中山日报新媒体中心
◆编辑:徐向东 实习生 郭君宜
◆二审:曾淑花
◆三审:岳才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