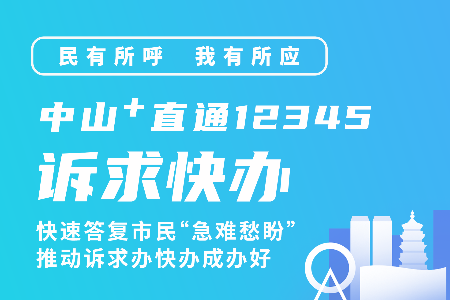候鸟
冰封的河面,在散落的月光下,在春风的吹拂中,慢慢开裂。河边的杨柳细枝,悄悄地抽出嫩芽,贪婪地吮吸着绵绵细雨。松花江里的“三花五罗”们,在浮冰下敲着门,叮叮当当,提醒着困倦的人们春天的到来。
三五成群的孩子们终于可以甩开帽子、围巾和手套,撒欢儿似的在江边放着风筝。那风筝却也飞得不高,懒洋洋地陶醉在春烟迷蒙中,曼舞在湖蓝的天空。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就盼来了从南方小城来的外公。他如候鸟一般,春来秋往,带来我垂涎已久的南方风味。每当他风尘仆仆而来,刚一进家门,还没摘下帽子,我就冲上去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甜甜地喊声“姥爷!”这一抱,从我张开手只能圈着他的双膝,到窜起来能搂着他的脖子,细细算来,总有十几年的光景。外公每次都一边不好意思地往后退,一边蹲下来迎着我,嘴角抿着笑说:“姥爷身上脏!”“都是大姑娘了!”可我知道他心里已经乐开了花。抱过之后,我就急急地去搜罗他包里的美食了。这其中我最爱的,是辛辣甜香的多味花生,它们总是被我藏在书桌下面的“保险柜”里,红红绿绿的一大捧。我望着它们,心里流淌着快乐的小河。每吃完一包,就拨弄着手心的小算盘,十包、九包、八包、七包。于是,渐渐愁眉苦脸起来,似乎东西吃完了,就到了外公回南方的时候了。所以,到了最后几包,我总是舍不得吃,也不敢算日子,连挂历都不想看一眼。好像,我瞧了一眼,时间就会快马加鞭、扬起尘沙,把人远远地甩在身后。南来北往的火车就在和风细雨中来,秋风瑟瑟时去,我追不上,也看不见。那个每年在外公的背上,辗转三千公里的红蓝编织袋里,装着的不只是我一岁的滋味,更是我一年的期盼。
二月的雪落迎春,三月的春燕绕梁,四月的麦花雪白。一年的好光景,在万物悄无声息地恣意生长中流淌。这年的春天,两只小兔子成了我们家的新成员,毛茸茸的一团团,可爱极了。每天放学后,我就缠着外公一起去江边打草喂兔子。挎上个竹篮子,跟着爬山虎直出胡同。借着一排排榆树的阴凉,一边嗅着杏花,一边追着风一路小跑就来到了江边。我也没等外公,一个人在前面疯跑,不一会儿,后面就传来由远及近的喊声“孩儿,慢点儿!”听声音我就知道外公肯定撇着两只大脚乐呵呵地跟着我呢。江边上,紫花的苜蓿、黄花的蒲公英,藏在一片悠悠碧草中,我蹲在地上仔细地搜寻,就像欢乐的鸟儿在啄着稻谷,找到一株就满心欢喜,朝着外公大喊“姥爷,我找到了!”待我满满的装一篮,外公的歌声也一浪高一浪在身后飘。
天上升起一弯月牙啊
月牙弯弯正把那个月光洒
人都管月牙叫月老
直唱得太阳歪歪斜斜,脸也红起来,不一会儿就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躲到云朵后面去了。到了斜阳西照时,一高一低两个影子,拉得长长的。时间仿佛静止,我心中盈满喜悦。后来,每每回忆当时的画面,我常常在想:夕阳啊,夕阳,你能否把时间也拉得长长的,把外公在病床上苍老枯黄的三五十天变成三五年,变成他最帅气挺拔的那几年,就像那张泛黄老照片里穿着海军制服时的模样;亦或是我童年里,他带着螺纹草帽、穿着有洞的白背心,笑声朗朗、歌声涛涛的那几年。然而,我在他的病床前,拍着他当时骨瘦如柴的肩膀,对他说的“姥爷,等我下次回来看你,你肯定就好起来了!”竟成了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人生聚散离合,生命荣枯,如手中细沙,山中溪泉,一切不可挽留,终是无法改变,候鸟终究是要春来秋往。
日月沧桑,时间调拨着琴弦,掌管着万物的轮转。有嗷嗷待哺的雏鸟,就有垂垂老矣的苍鹰。一朵花开,跟着蜂蝶戏舞;一片叶落,跟着白雪纷飞。万物轮转,永不停歇。而外公的时间轮盘,在我二十九岁的秋天,永远地停了下来。一群大雁自北向南,在橘红色的落日里,朝着江心落英缤纷的小岛缓缓而落。疲累的鸟儿最终寻找到了它的归宿,平和而安宁。
◆中山日报报业集团新媒体中心
◆编辑:徐向东
◆二审:韦多加
◆三审:魏礼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