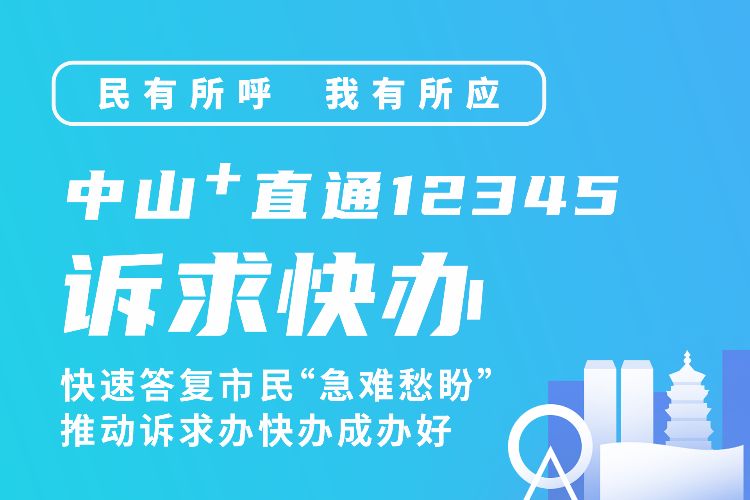“喔,喔,喔……”堂屋角落鸡窝里的公鸡一打鸣,母亲就摸黑起床烧水,父亲则提着马灯去请屠夫和叔叔。

昨天下午,母亲就洗干净了日常煮猪食的大麻锅,用来烧杀猪的水。随后,我和哥哥就挑水倒满了它。
养猪,是家里经济支柱之一。一年里要分好几批卖出好几头大肥猪。有些年,家里还养了母猪,喂猪崽卖钱,以增加收入。
父亲一般分三个时间段,分别从集市上买回猪崽饲养,喂到足够大的时候,恰巧是过年、开春和秋天开学这几个集中需要钱的时节。
乡亲们对杀猪是很重视的,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香烛,纸钱不可或缺,虽然迷信,倒也凸显了心底对“二师兄”的歉疚和感谢。
杀猪前天,家里必须准备一张结实一点的板凳和两个木杈。请屠夫过来的时候,一定会把师傅的工具一并带回:尖刀和砍刀各一把,拉钩和刮子各一个。
屠夫到前,过来帮忙的叔叔已在等候。这叔叔不但孔武有力,而且还得懂得捉猪尾巴的技巧,村人杀猪都请他帮忙。
水一烧开,母亲立马知会陪师傅和叔叔喝茶的父亲。他连忙起身把板凳放置在猪圈门旁,把树杈靠放在屋后的窗户边。
屠夫和叔叔也放下茶碗,正式工作。只见穿水鞋的屠夫,抬腿跨入猪圈,左手顺方向轻摸猪背,拿钩子的右手突然一伸,拉钩侵入猪嘴,嚎叫声马上划破夜空。
这档口,帮忙的叔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捉住猪尾巴并往上提,令猪后腿无法着地,父亲也迅速及时地抓住了其中一只猪耳朵,与屠夫一起牵着猪头朝猪舍外面疾走。
这个时候,屠夫大声叫喊:“她婶婶,她婶子,快……快点,快把板凳换个方向!”随后,把猪拖上了换过方向的板凳。又见其两腿前弓后箭,左大腿抵住猪头,左手按住猪头,右手捡起准备好的尖刀,猛地刺向猪脖子,顿时,猪血喷泉般射向备好的大盆里。
这一连串“快、准、狠”的动作,衔接得天衣无缝,不愧是杀了二十年猪的老屠夫。
我非常好奇,为何这么急切地要求把凳子换方向。他犹豫许久道:“屠夫有两不杀,一是五爪猪不杀,因为它已修得五指;怀孕母猪不杀,否则罪孽深重。”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乃万物之源。之所以要求换方向是因为先前凳子朝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这对太阳公公大不敬。
去毛、开肠、破肚、肢解,再入箩筐,一番下来天还没有苏醒。父亲已经快捷地张罗了六个新鲜菜,现宰现煮的“硬菜”,平常不多见的“硬菜”。
奶奶已经起来,父亲每煮好一道菜,她就分别端到大门口和神龛前,举过头顶供奉天地君亲师和祖宗,口中“哩哩隆隆”地嘀咕着,大概是邀请他们享用,祈求他们保佑。
杀猪的这段时间,是家里生活水平最高的时候。每回杀猪,必然留下猪板油,乡亲们叫猪膏肉,这是猪身上油水最丰盛的地方,榨出来的油足够全家近两月食用。
即便剩下的猪膏肉渣,与剁辣椒一起,放上点姜沫,撒上点葱花,吃起来也妙不可言,不但是家里招待客人的“大菜硬菜”,也是我们上学时候玻璃瓶子里的美味佳肴,更是乡亲们开春后下饭的上等极品。如今县城的饭店酒楼里,仍然有这道菜,非常畅销。
杀猪的日子,也是孝心体现最显著的时候。父母亲老早就会把爷爷奶奶和外公请过来,把猪心、猪舌、猪腰等稀少的东西,切细煮好,匀称地给他们分享。
杀猪的那天,也是家庭和邻里联谊的最好时日。乡亲们深谙“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天会伯伯叔叔们请过来围上一桌,吃着新鲜的饭菜,喝着农家自酿的红薯土酒。
杀猪的这一天,乡亲们还会把猪血东家一碗西家一坨地送。不管曾经吵过还是骂过,不论之前打过还是恨过,大家都能相对一笑泯恩仇。
杀猪,在儿时的老家,就好像春节、中秋和端午的节日一样:繁忙、热闹、正式、隆重。可惜的是,离开家乡已经好多年,老家的样子越来越模糊。
去年春节前,父亲六兄弟中唯一留守老家的五叔,盛邀我们回家过节。行走于老家的角角落落,青砖黛瓦的祖屋已经倒塌,低矮的猪圈、羊圈和牛栏也已经破败不堪。满眼的残垣断壁,朽木瓦砾。牛羊成群猪满栏,鸡犬相闻鸭戏水,也只是一种印记。
祖屋旁,一幢幢钢筋混凝土小洋房里,传出来的字牌落桌声、麻将碰撞声已经取代了杀猪的嚎叫声。
◆中山日报报业集团新媒体中心
◆编辑:徐向东
◆编审:岳才瑛
◆素材来源:中山日报